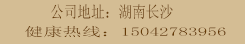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新闻 > 美原中学校友快来签到啦那些年,留在母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新闻 > 美原中学校友快来签到啦那些年,留在母

![]()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新闻 > 美原中学校友快来签到啦那些年,留在母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新闻 > 美原中学校友快来签到啦那些年,留在母
那些留在美原中学的岁月
文/康利莹
似水流年,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昨。年,我12岁。因为机缘巧合,我进入美原中学,开始另一段求学生涯。这也是令我终生受益、永远不能忘怀的一段美好时光。在三年的初中生活里,我们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跟随一群踌躇满志、才华横溢的老师,学习、生活、游乐,在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互帮互助中,学习文化、认知世界、陶冶性情、参悟理想,从而奠定了我们一生做事、做人、修业的基本功,造就了我们善良、友爱、奋进的品格。
每每提及初中时候接受的教育和学习生活,总认为,我们在人生的启蒙阶段,幸运的遇到了最好的老师;而我们的老师,也在他们年轻的从教生涯中,遇到了最好的学生,成就了一代名师。文章里所写的点点滴滴,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感受,也从自己40年前的初中日记中得到印证。在这一点上,还要感谢我们的老师和我的母亲。在初中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养成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以便日积月累提高作文水平。所以,三年的初中生活,被我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更要感谢我的母亲,因为对老师、对知识、对书本的敬重,她保留了我初中以来所有的学习资料,尤其是几十本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纸质各样、字体不同的日记本。仅仅就是这些本子,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再看看里面稚嫩的语句、字迹,初中时代我们的生活跃然纸上。上课的情景、课余的活动;考试的紧张、节假日的欢快;攻克难题的喜悦,分数失利的自省;书法作文的训练,诗歌小说的赏析;雷锋事迹的学习,建设祖国的设想;春日里桃花园的踏青,夏天时金粟山的攀登;操场上篮球排球足球的竞技,教室里功课朗诵歌唱的比拼;日升月落的四时变换,花红柳绿的自然风光;街道乡邻的生活描写,忧国忧民的感想思考......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看着看着,竟也羡慕起当时的自己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拥有了如此丰富、快乐的学习和生活。稚气未脱读书郎。当时我们两班学生总共在90人左右,一个班大约45人。开学第一天,就是排座位。男生女生按照个头大小排成两行,两两一桌,很快排好了座位,教室前面集中坐着一群小不点。可就是这些个头不高的同学,让我们在日后的学习中丝毫不敢小觑,成为追赶超越的榜样,其中出了几位博士、大学教授。我呢,当时属于个子比较高的,坐到了教室后面,结成了一帮自己的姊妹团。座位定期1与、2与4列进行交换,每次换完都有一阵新鲜感。戴近视眼镜的同学印象中没有几个,所以根本不牵扯到特别的照顾。那时候,任何事情都比较简单。食宿。当时的我们,大多是农家子弟,穿着粗衣布鞋,背着黑面馍馍,吃着辣子蘸盐,睡着木板通铺,谈着的却是建设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同学中家境好点的,炒点咸菜疙瘩用罐头瓶子装了带着,或者在灶上交上一点粮食,买点菜票,能吃个热乎饭。绝大部分同学,都是一人一个大瓷缸,下课了跑去水灶上舀点开水,掰点馍馍往里一丢,加点盐巴,呼里呼噜就是一顿饭。当时的年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开水泡馍难以支撑到饭点,于是在上课的时候,就常常有同学,在桌子抽斗里悄悄地放上一张纸,撒上辣子盐巴,掰点馍馍偷偷蘸着吃。吃得忘形的时候,就是被老师发现的时候,一个粉笔头准确无误地就过来了,往往引起一阵哄笑。那个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是苦,能够上学,就已经很幸福了,还有许多同龄人还上不起学呢。
夏天了,有不少同学嫌宿舍人多闷热,直接睡在了教室,两张书桌一并就是床铺。常常有到校早的同学都到教室了,寄宿的同学还在后面桌子上酣睡,调皮的同学还趁机给画个花脸,惹得哄堂大笑。天气最热的时候,值日生就一盆一盆地往教室地面泼水降温。冬天了,一群孩子挤在教室外的南墙上晒暖暖,有的脚对脚踢着蹦着暖和身体,有的相互用冰冷的手逗着玩。那时候,有许多同学的手冻出了冻疮,老师就用花椒杆煮了水,端来给同学们泡手除冻疮。那时候卫生条件比较艰苦,书桌里也经常有臭虫,咬的人身上一个个大疙瘩,老师也经常带我们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晒桌子、晒床板、晒被褥。
意气风发青年师。几位老师带我们的时候,非常年轻,每个人性格鲜明、隽永洒脱,教学风格迥异,堪称典范。第一位班主任付银善老师,和蔼儒雅,数学课教的非常棒,以至于后来调走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学都舍不得,哭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刘宝全,本身就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刘老师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一点一点的学,一个一个单词的背,把一门英语学得滚瓜烂熟,并由此走进学校,成为教学有方的“先生”,还写得一手大气端庄的隶书。教我们体育的韩老师,虽然黑黑瘦瘦,却爽快利落,教我们打排球篮球、踢足球,三大球开战的场面一度非常吸引人。经常是在下午,班主任老师直接锁了教室门,强迫大家走向操场,进行体育锻炼。两班几十号学生,连同老师齐出动,在一个足球场上,盯着一个皮球,满场飞跑。常常一脚踢起,足球飞上了天,顺带的还有鞋子也上了天。当时的体育课设置还是非常丰富的,三大球样样都有,体操、武术、短跑,老师全教。学校有排球队、篮球队、田径队等,定期训练,我们两班的不少同学都是队员。印象深刻的还有教数学的向老师,一次公开课上,徒手执一支粉笔,“唰”一下,在黑板上画出了一个大大的、规规整整的圆,惊奇得我们张大了嘴巴,瞬间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地听完了我们不懂的公开课。老师中,最有影响的,是我们两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祁吉寿、数学老师惠西胜。一个豪放洒脱,一个治学严谨,所以,两位老师带出来的班级的学生,也风格不同,我们班的同学热情活波,二班的孩子认真内敛。我们的班主任祁老师当时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讲话出口成章,文采斐然;上课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堂课每每在意犹未尽中结束。而惠西胜老师,治学严谨,一脸严肃,在他的课堂上,少有敢捣乱不听的。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不认真听讲,老师毫不客气地用黑板檫打过去,批评他“枉披了一张学生皮”(那时候老师教育学生,家长是不会提出任何异议的)。
灵活多样育才途。作文。为了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要求每天写日记,每天做一个同学的肖像描写,互相读着看像不像,每天出操时背诵一首古诗。博闻强记,老师硬是在那个书本知识不很丰富的年代,用自己的爱好,引导我们额外学习了许多经典诗词、文学作品等等,培养了我们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习惯。我们在文豪泰斗的绝句中,游历名山大川,体会高远意境;在经典散文诗歌中,品味社会时代变迁,领悟艺术来源生活。至今,许多文章诗歌依然脱口而出。为了激发写作灵感,老师带我们去踏青、去爬山、去赏花。组织大家描写活动的情景、畅谈自己的感受、想法,开展作文现场比赛,一个个小作家、小诗人应运而生。至今还记得在金粟山上,我们两班的同学,各自手拿山花,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依次逶迤而行,林中不时有蝉儿、鸟儿发出几声鸣叫,伴随童声笑语,飘荡在山谷中。好美啊!一下子就体会到了老师讲解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在我的日记中,还保留了许多老师的评语,有教给习作方法的,有赞许鼓励的,有批评指正的。红色的蘸水笔,遒劲有力的字体,字斟句酌的批语点评,体现出的是我们的老师,对学生一点点的进步与退步、对每一篇作业的十分用心。写字。参加工作后,许多人一看我的字迹,都感慨不像是女孩写的,我也因此洋洋自得,这同样受惠于恩师。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祁吉寿爱好书法,写得一手飘逸潇洒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强调字如其人,要求我们规范字体,每周写2张毛笔字,张钢笔字,定期上交批阅。常常是,我们在讲台下静悄悄的上自习,老师在讲台上练书法改作业,也常常见老师在办公室门前的砖地上,用毛笔蘸了清水,练习大字。老师后来也成为陕西有影响的书法家。赏析。这两年,董卿主持的《朗读者》如一缕清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灵。40年前,我们的老师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引导我们畅游在名言典故里、文章辞海间、诗歌小说中,同样激情洋溢、同样扣人心弦。每天出早操时,老师教给大家一首古诗,要求我们一边跑步,一边背诵。于是,在美原中学的大操场上,黄土弥漫,童声朗朗。几圈跑步下来,广播操做完,一首古诗就被我们牢牢记住。“我以微笑告别历史,手牵着儿子跨出柴门”,这首流沙河的《故园别》,老师朗诵时的惟妙惟肖、解读时的眉飞色舞,都历历在目。晚自习,遇上停电,我们两班的同学就集中一起,一条长凳上挤4位学生,一个教室近90号人,就着烛火,静静地听老师诵读《梅花档案》等自抄本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身临其境的描述,听得我们如醉如痴,在回家的路上,还常常被其中的细节吓得瑟瑟发抖。解题。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两班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永远都有一板题在等着我们去解答。每天上自习的时候,数学老师惠西胜,都会在后面的黑板上出一板题,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自觉地向后转,一边抄写,一边解答;讲解的时候,两班的学生一集中,就其中的知识点、难易度进行重点说明,一堂课干净利落讲解完毕,有时还让数学好的同学给大家演示。之后,另一板题就又抄在黑板上了。这样日复一日,高强度的练习、讲解,使得我们的学习效率、学习成绩大大提高。改名。那时候,同学们的名字都是很有时代特色的。如前进、社教、军武、栓牛、进虎、小艳等等。名字虽由父母取,但老师用自己的大智慧,还是为一些同学改了名。如井涛,原名井前进,老师说,你姓井,如果要取得一些成绩,必须能够翻起浪花,所以改名井涛;还有乔栓牛,老师说,栓牛表明力量大,改名为乔力;关小平,更名为关华;王小丽改名为王琰;许小娟改名为许娟;杨自绪改名为杨琦。不知是不是得益于改名,后来这些同学,都成为各自行业领域里的佼佼者。
言传身教惠人生。老师们的行为习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因为敬佩老师,在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有二十多位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师范学校,成为八十年代最早的师范生之一,从事着教书育人的光荣事业,承担起乡村教育的重任,今天也大都桃李满天下。从老师们的身上,我们也学会了对一切人和事物的尊重。当年老师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对家庭贫困的学生更是多关心几分;课堂没有听懂的,放学后专门留下来补习功课。看我们的初中毕业照,就连水灶上的李师傅也端坐在正中间,倒是我们两班的班主任老师,挤在了最边上。老师要求的写日记的习惯,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年来,无论是学习、工作,都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也练就了自己写文涂鸦的技能,得益进入集团总部大平台;也因为这份坚持,陆续有宣传报道、散文论文、实践成果在报刊杂志刊载获奖,工作也得到领导同事支持认可,获评陕西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以及集团第一位正高级政工师。每每取得一点点进步,都十分感念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也感慨今日国内教育之偏差。教书育人,是需要有担当的才华和高尚品格的。老师和我们之间,亦师亦学亦友,一路相携。
作者简介:康利莹,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爱好写作。
难忘美原中学:我的零点起步文/李郁
我的母校美原中学,简称美中,是富平县最著名的一所高中,上世纪80年代一度创造了全县最好的升学率。
那时候,考取名校的美中学生很多,其中不乏北大、复旦、同济、中山、陕师大、西大、兰大等全国著名高校。我当年也考得不错,天随人愿,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我从美中走出来,见识了更大的世界,视野渐渐变得宽广。
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测试题:此生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此生最难忘的事是什么?此生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
我曾经将这样的问题复述给我的孩子,他的回答很简单:「我还小。问我妈。」他的妈妈则指着他说,「影响我最大的人是你,最难忘的事是生你,最艰难的时期是养你。」她说的真的很实在。
那么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说,「影响我最大的人是高中老师,最难忘的事是高考,最艰难的时期是高中时期。」他们不明白。我解释说,「人生最关键的时期正是高中时期,最艰难的时期也是高中时期。高中苦三年,享受一辈子;高中逛三年,辛苦一辈子。没有比高中更重要的了。」
美中是我的窗口。我从美中的窗户爬出来,最初的大学几年真的很享受,然而此后的路却并不好走,而且越走越难走,越难走又必须得走。我多少次想要放弃,但是只要想起美中的那几年,我便觉得所有的苦算不上是苦,所有的难更是算不上是难,所有的煎熬只能说是一种历练。
美中位于富平的东北古镇美原。美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秦朝开国大将王翦、王贲父子的封地,因其有美田千顷、原野丰饶而得名。
如今的美原中学教学楼
上世纪70、80年代,在富平的北部有三所高中,从西往东分别是薛镇中学、美原中学、老庙中学。其中以美原中学的历史最长、师资力量最好,当然教学质量也是最好的。
我们上学那一年,美原中学在几千名初中生里一共只招收了六个班的学生,大概不到三百人,几乎是十分之一的比例,可见农村学生上学的难度有多大。当时,能够上高中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那时的师资力量极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全校公认的好老师之一,优秀如此,也没有大学文凭。其他代课老师中,有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些则是临近几年才培训的临时代课老师。
那时候,教师有民办公办之分。好些老师在学校上课,只拿一个月几块钱的生活补贴,其他的待遇就是记工分,一天记8分还是10分。年终,老师们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领取钱粮,往往入不敷出。但是,他们敬业,他们一边学一边教。
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心中的目标也只有高考——高考成绩好了,学生似鲤鱼跳了龙门,老师们欢天喜地,和学生们的父母兄弟一样高兴。
学校的教室是那种宽敞的大房,砖瓦土木结构,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只有房梁上一前一后的几盏大灯泡。夜里按时熄灯,10点还是9点半,不记得了。
正式熄灯前,有一个预熄灯,提醒大家做好准备,中间的间隔大概是几分钟。可是,管灯的师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延长熄灯的时间。我们因此能够多看一会儿书。
那时候,只要预熄灯一灭,同学们就会快速地收拾好书本,放在手边,然后拿着一本书继续学习。
熄灯后,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昏黄的路灯有些许的光亮。大部分同学回了宿舍。有些同学却就着路灯继续看书,直到值班巡夜的老师再三提醒该回去睡觉了方才离去。宿舍也是按时熄灯的,有些同学睡不着就拿着手电筒,偷偷地钻在被窝里看书。
学生宿舍里是大通铺——几十公分高的木板床分成两边,中间留出过道,几十个人一人占一个床铺,大约有被子那么宽。被褥都是学生自带的。白天,被子叠起来被整齐地放在一起,晚上,学生们一个挨着一个睡。同学中没有太胖的,并不觉得挤。
每个人的床头不高处必有一枚铁钉子,那是用来挂自己背的馍包的。装馍的布包很大——学生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必须拿够六天的干粮。每天每顿饭必须计划好,吃多吃少完全靠自己,如果一顿饭不小心多吃了半个馍,下一顿就得少吃半个,否则挨不到星期六。
学校有大灶,但是粮票是补助的,非常有限,只能挤了去打些玉米稀饭。虽然稀饭常常有一种焦煳味,但总比白开水泡馍就咸菜辣子好许多。稀饭是在那种直径至少有1.5米以上的大铁锅里熬的。
学校偶尔提供些炒的玉米面饸饹,那是一个星期里最好的饭了。不过,只有拼命挤进去,才能打上一小碗而已。
学生们的家离学校有远有近,最近的住在美原街道上,最远的大概是住在北山里的。
我的家距离学校十里路,不算很远,来回两个小时。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去,能吃一顿饭,然后背馍回校,星期天补课或者自习。
补课是老师自愿的,不收一分钱。那时候,老师常常将课外作业手抄在备课本上,然后再写在黑板上。晚上,老师批改完作业,再将问题罗列出来,一个一个反复讲解。
怀旧老课本
当时,全国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历史、地理和政治等课程也不甘落后。唯独英语是新开的,用的是试用课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篇文章选用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的一段关于邓发的片段。
老师们教导我们奉献的理想和学习的责任,也教导我们做人的根本。我记得马可闻老师给我们讲述「罢了」的故事,教我们学会知足和达观的理念;田遇中老师教导我们慎重地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不要为了一时的苟且取巧而陷入短见和意气用事;王忙寿老师激励我们不要怕苦、积极进取、要敢于向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名校冲刺。
几十年来,我一直觉得我们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遇到了一批敬业、有良知、无私奉献的好老师,也深知国家待我们不薄,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是免费。我常常想,如果要交学费,我肯定没有学上,更不用说上大学了。
体育课是必须的,那时的教学理念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整天吃不饱,即使吃得饱,也大多营养不良。所以,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们的体育课就很少正常上课,老师也不很在意。这样既节省能量,又腾出时间看书学习。总之,文化课学习才是第一位的。
即便如此,每天的出操却很正常。学校操场的正北方有一个宽大的木板门一直关着。我们每个星期要绕很大的一圈从南校门出去再绕到北面去,最少要花费20几分钟时间。我每个星期都渴望那座门能够打开,给我们行个方便。但是从来没有。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偷偷翻过那个门了,但是,我肯定有过翻墙越门的「非分之想」,要不然至今我还耿耿于怀呢。现在,我坚持「能与人方便便与人方便」的信念,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
回家的路走得多了,便有了同行的伴儿。那时候一个村也就一两个高中生,很少在一个年级,更不用说分到一个班了。所以常常是同班邻村的两三个人走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两个人拿着单词本背单词或者互相提问问题,一问一答,时间很快就能过去。还能约好时间一块儿返校。上学的几年里能结交到最铁的哥儿们,互相激励着考上大学的人非常多。不仅如此,每当课间,也能彼此提问、互相解答。
读书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不读书毋宁死。大概是那个时候养成了阅读的习惯。
到了大学,我发现我的周围怎么都是这样的主,而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觉得比他们差了很大的距离。于是我恶补了两年的读书,才逐渐缩短了距离。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高中时养成的读书习惯,大概我老早就被淘汰了。
美原中学校园内繁茂的「合欢槐」
时间走得太快,很多年过去了,美原中学的艰辛历程却总是萦绕在我的心际,幻化成那种催人奋进的精神。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能够想到:如果拿出高中时候的三分之一精神,天下还有做不成的事吗?
丙申初春,有人写了一篇微文《适时让自己归零》,非常之好。我归了零,就回到美中。从零开始起步,我希望我的心能够如此。
作者简介
“李郁,陕西三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编审、副总编辑,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从事编辑工作近0年。
”如今,时光一去不复返!年注定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刚刚度过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期,
如今又面临撤并美原中学,
这一令人伤感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
如今偌大的校园只剩高三学子,下一步会怎样,我们心中似乎都已明确身为富平人、身为美原中学的学子,你作何感想?撤并美原中学,
非人为之过,
而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美原中学的校友们
希望你们永远牢记你们曾经的母校
---美原中学!
也欢迎美原中学各位校友留言
诉说、分享你关于母校的青春回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xw/62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