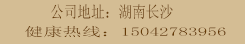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文化 > 民间记录墓志的演变与上海墓志特征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文化 > 民间记录墓志的演变与上海墓志特征

![]()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文化 > 民间记录墓志的演变与上海墓志特征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文化 > 民间记录墓志的演变与上海墓志特征
墓志从最初的仅仅用来记事和标识墓地的实用文字发展演变为一种纪实、颂美兼备的文体,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受到士人群体的青睐,成为丧祭礼仪必备之物。就上海地区而言,墓志在明代得到空前发展,之后渐显式微。进入当代社会,人们对传统墓志已越来越陌生,在墓志铭的撰写方面也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下面就墓志的演变与上海墓志的特征作一概述。
一、墓志的演变
这里的墓志乃广义而言,包括与墓主同葬于墓穴中的墓志,以及表于外的墓碑、墓碣、墓表等。埋铭、圹志、圹铭、葬志、墓记等皆为墓志异名。
墓志本属碑文的一种。碑在古礼中最初只是木板,用来观察日影以定晨昏,所谓“宫庙皆有碑,以识日影,以知早晚。”《礼记.祭义》云:“牲入丽于碑。”“丽”即“系”之意,将牵祭牲的绳子栓在碑孔中,待神飨之后,再杀以血祭。此为碑与祭祀之关系。春秋时期,碑和丧礼发生联系。最初也只是凿了窟窿以穿绳装辘轳的木柱子,以便棺椁入墓。《礼记.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视丰碑。’”注云:“丰碑、以木为之,形如石碑,树于椁前后,穿中为鹿卢绕之纤,用以下棺。”碑本为木柱,周代仅天子可用石碑,诸侯不敢;周末诸侯改以石为之。周碑不刻文,或弃置墓旁、或埋入墓中。秦汉以来,死有功业,则刻于上。晋宋间始称神道碑,大概是因为地理堪舆家以东南为神道,碑立其地而命名的。
按古礼,五品以上官员葬有丰碑,葬者既为志以藏诸幽,又为碑碣表以揭于外。碑之文体有文,有铭,又或有序;而其铭或谓之辞,或谓之系,或谓之颂。文与志大略相似,而稍加详焉,故有正、变二体。其名称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铭,或曰神道碑铭并序,或曰碑颂,皆别题也。至于释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拟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铭,或曰塔碑铭并序,或曰碑铭并序,亦别题也。古者碑之与碣,本相通用,后世乃以官阶之故而别其名,五品以下官用碣,其实无大异也。其题有曰碣铭,有曰碣,有曰碣颂并序,皆碣体也。墓表文体与碑碣同,有官无官皆可用,不像碑碣有等级限制。因其树于神道,故又称神道表。又取阡表、殡表、灵表,以附于篇,则溯流而穷源也。盖阡,墓道也;殡者,未葬之称;灵者,始死之称;自灵而殡,自殡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1]由于碣表揭于外,同时也因为已有墓志,故而墓主家世、生卒等具私密性的内容就免于刊刻了。如明代归有光所撰《赠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吴君墓碣》中言“余与君之子为三十年交,因知之详,遂不辞其请而书之。其世次生卒别有载,兹不具云”。再如清代钱大昕所撰《文学乡饮介宾曾君墓表》中载:“翁名某、字某某,其行事卓卓者,多见我祖所为志铭中,此论其未尽载者。乌乎!翁自是其可传也已!”
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中指出:“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其书法,则惟书其学行大节;小善寸长,则皆弗録。近世弗知者,至将墓志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然无其美而称者谓之诬,有其美而弗称者谓之蔽。诬与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欤!”[2]可见,碑碣同墓志在书写内容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侧重,墓志重实,而碑铭重文。就人口学研究而言,墓志比碑碣更有价值。
墓志体例多种多样,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指出:“至论其题:则有曰墓志铭,有志、有铭者,是也。曰墓志铭并序,有志、有铭、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志铭而或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者,则别体也。曰墓志,则有志而无铭。曰墓铭,则有铭而无志。然亦有单云志而却有铭者,单云铭而却有志者,有题云志而却是铭,题云铭而却是志,皆别体也。其未葬而权厝者曰权厝志,曰志某;殡后葬而再志者曰续志,曰后志;殁于他所而归葬者曰归祔志;葬于他所而后迁者曰迁袝志。刻于盖者曰盖石文;刻于砖者曰墓砖记,曰墓砖铭;书于木版者曰坟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志,曰志文,曰坟记,曰圹志,曰圹铭,曰椁铭,曰埋铭。其在释氏,则有曰塔铭,曰塔记。凡二十题,或有志无志,或有铭无铭,皆志铭之别题也。”[3]
我国墓志文化历史久远,早在周代产生的“明旌”就是标识墓主的丧具之一,二字急读称“铭”。《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己,故以其旗识之。”又,《仪礼·士丧礼》云:“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赦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枢”。郑玄注:“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其旗识之…。”汉时,明旌在出丧时作为蟠信在棺前举扬,而入葬后则覆盖于棺上。《礼记·丧服小记》云:“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可见,铭旌具有一定的文体格式,士以上的等级,直至天子,其文辞风格同一。
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认为,刻辞之碑“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卢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东汉后期,厚葬之风盛行,天下葬死者奢靡,相互标榜,竞相夸耀,以至累及民生。至“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两晋沿袭曹魏禁碑之令。因禁令极为森严,皇戚官僚、士族豪强皆不得立碑,只能变通将墓碑做小,放置于墓扩。然而,社会上已形成一套世代相传的丧葬习俗,特别是用铭刻来标志墓葬的观念。于是,人们就更多地采用变通的方法,把文字铭刻转入地下,故南朝常以墓志替代碑铭。中原地域,汉时人多于墓前立碑,至魏晋方禁碑不止,为北朝时兴墓志埋下伏笔。东晋王朝迁至江南仍承接禁碑遗风,但屡禁而屡弛。北朝未有禁碑,孝文帝反而倡导立碑。中原顺应墓志之礼俗,北方鲜卑亦尾随汉人推波助澜。于是乎北魏时兴厚葬之风,朝廷对臣僚葬事大行赏赐,此乃北朝墓志碑铭勃兴的机缘。这一时期墓志渐趋定型化,在刻制工艺上已很考究,形制上多作方形,两石相合,成函盖式,平放墓中,上面为志盖,文字作篆或隶,亦有真书,尤如碑之额;下则为志身,开头有首题,文体上有志传文与志铭文,后或有尾记。自此,永为定式。这是中国历史上墓志形成定制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这一时期,为日后中国特有的墓志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础,绵绵一千余年,成为各代丧葬礼俗中主要的墓中铭刻。墓志的制作工序大体包括选材、志料规整、预画界格(包括格式设计)、墓志文写作、志文书丹或摹勒、雕刻(包括绘制纹饰)等若干步骤,一般是由丧家、志文者、书家、工匠共同合作完成。墓志选材及其尺寸大小是有一定制度规定的,一般不得违反礼制而发生“僭越”现象。
自清末始,墓志文化走向衰落,出土墓志数量的锐减也可佐证这一事实。近代以来,由于一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墓志也被看作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遭到否定,传统墓志文化几近湮灭。现代人对于传统墓志已经非常陌生了,一般理解的墓志铭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保留传统特征的墓志铭与传统定式的墓志相比,差距也很大,特别是在家族人口记载方面有很大的漏缺,志文内容多为墓主本人的简历与功绩。
当代墓志(广义而言)的主要形式就是墓碑,一般不会有埋在地下的墓志。综合上海地区墓园的实际调研以及墓志铭碑文网[4]提供的内容,当代墓碑文大体上可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大类。就传统型墓碑文而言,这种碑文从文字语言到所记述的内容,都与传统墓志铭类似,因其表于墓外,故其某些家族信息不便于尽书其上,所以与传统的墓志有些差别,但总体风格较为一致。这也说明了传统墓志文化在民间的影响。传统型墓志铭文字优美、内容丰富,对墓主的生平与德善都有记载,碑文不仅可供后世子孙了解先人的身世阅历,构建生者与逝者的“对话”平台,更可以通过文字寄托生者的哀思,以致祭礼,传承中华文化的“孝道”美德。但由于此类碑文对撰文者的文化素养要求较高,所以此类碑文较少,有些碑文尽管仿效传统墓志文的写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难掩瑕疵。就现代型墓碑文而言,因现实语境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现代型墓碑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碑文没有固定的体例,可长可短,可简可繁。从碑文的内容看,有逝者的简历,有子孙、亲友的寄语,有逝者生前说的话或自撰的墓志铭,还有就是具有哀悼性的纪念墓碑文。笔者以为,现代型墓碑文还在发展之中,还未形成定式,有些研究机构也在探索适应当代社会的墓碑文。无论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墓碑,其正面一般刊刻墓主姓名、生卒以及子女等家庭成员情况,墓碑背面或墓前其它石刻上刊刻墓碑文。
从上海墓园的实际调研来看,除上海福寿园外(园中安葬的多为社会名流),多数墓园中的墓碑仅刊刻墓主姓名、生卒以及配偶、子女等信息。其它类似墓志的碑文很少,即使有,也多为寄语型碑文,文字少,而且比较简单,并且表现出程式化的特征,如“思念”、“福佑子孙”、“光照后代”等这样比较单一的寄语碑文。
而传统墓志自魏晋南北朝形成定式以来,一直保持其相对固定的体例。本研究中明清墓志样本也充分地证实了这种特点,墓志中不论志文多少,都会记载墓主世系、生卒、婚配、子女以及其本人的德善功烈,德善记录以其孝悌睦族的家族乡党生活为主,而这种生活记忆本身同其子孙后代具有亲密的联系,因此,传统墓志就成为生者与逝者“对话”的平台,逝者的人生阅历也会通过文字转化为智慧,启迪后人。
通过比较,笔者以为当代墓志文化因传统文化的一度断裂而造成一定的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上海墓园的调研可知,大多数的墓碑仅仅是一种标识,有关墓主生活记忆的记录非常之少。一些社会名流的墓碑尽管多有文字记录,但也多以工作、成就、贡献为主,有关个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很少。这种墓碑或墓碑文难以搭建生者与逝者的“联系”,其子孙后代只有依靠个人的记忆去回忆与亲人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只能是碎片化的。“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这是祭祀的真正涵义,而当代的扫墓祭拜更多是流于形式,是遵循一种习俗,其内涵在逐渐消失,因为人们会失忆,从而失去与祖辈的“对话”能力,家族的智慧难以传承,子孙后代也难以从祖辈哪里受到启迪。
鉴于当代墓志存在的不足,笔者以为应该汲取传统墓志的精华,在墓碑文中保持墓主世系、生卒、婚配、子女以及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记录,以墓志承担其家史的功能。每年清明、冬至扫墓之际,可通过墓碑文搭建生者与逝者的“交流”平台,为传统祭祀习俗注入其真正的内容。这不仅可以充实丰富祭拜亲人的仪式,更可延续家族生命,使后人获得先辈的智慧,获得家族的归属感,获得家族文化建设的使命感。这无疑有助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也有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上海地区墓志概况
目前,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墓志为嘉定博物馆藏北魏神宗五年(年)《故归太原郡李氏(卢子真夫人)墓志石》,但该墓志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志文记墓主李氏为太原人,又“葬在城东岷山之阳”,显然不是上海本地所有。另外一篇较早的墓志是《南北朝吴郡征北将军海盐侯陆府君之碑》(见《松江文物志》),从志文记载来看,可算做上海地区最早的墓志。除此两篇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外,唐代墓志为14篇,宋代墓志为25篇,元代墓志为11篇。上海地区所能见到最早的出土墓志是青浦大盈乡的《唐故郁府君墓志》,系唐代宗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年)时的作品,这要比中原地区随葬墓志的年代晚了将近千年。根据周丽娟《整理新中国上海出土墓志的几点心得》一文,上海地区出土墓志的总体特征如下:
唐代墓志数量少,质地以砖质为主,大部分制作较粗糙;字体稚拙,因字的笔画多少、繁简,或大或小而不规范,以致满行字数不能统一;行文简率、短促,一般皆在一百字左右,仅记述死者姓名、籍贯、世系、生卒年月、葬地,还有的刻有有四字韵文。
宋代墓志,自称墓碑或墓碣、墓铭,大部分已使用石质材料制作,其主要形制为竖长方形,高大于宽。文字多为正楷,工整、规范,笔力遒劲,结体严谨,排列整齐,舒张有法。铭文篇幅一般较唐代长,铭文中包括死者姓名、籍胃、世系、职官、生卒年月、葬地,还记述了死者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文末大多有歌颂韵文。
至元朝仍以石质高大于宽的长方体为主,但顶端两角往往斜向截去。此时墓铭大都是楷体,文末大多不见歌颂韵文。唐宋元时期的墓志大多无盖。
到了明朝,才真正自称“墓志”,或“墓志铭”,在墓志撰写、书刻方面高度发展,形状为正方形体,青石为主要材质,由盖和底组成一盒,志盖多以篆书镌刻,底则是正楷或行楷书丹,字体优美。有些官位高的墓主人,其墓志铭文四周还镌刻云朵、花卉等纹样。墓主很多是当时上海地区的达官显贵,或著姓望族,以及具有一定社会名望的文人,代表着当时当地的上层社舍,故不少志铭出自有名望的大家之手。铭文的末尾基本多有颂辞。墓志形式也逐步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墓志铭,还有世系志、权厝志、寿藏铭等其它形式。
清代墓志形制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段包括清早中期,此时的墓志铭出现正、副本。按当时葬制惯例,下葬时正本墓志与棺木同时置于墓穴中,副本制作、镌刻的目的是为了传给子孙,故而一般藏于家中或嵌于家族祠堂的墙壁。所以我们见到同一个人的墓志铭往往有两种,一种是有盖有底相合为一盒的正方形正本志石,另一种则是宽大于高、呈长方形的副本志石,无志盖、志底之分,志首用篆书或隶书撰写,志文用楷体书丹。正副本内容基本相同,偶而也有些出入。如青浦博物棺收藏的乾隆四十四年()《皇清诰赠资政大夫大理寺卿王公墓志铭》就有正、副两本之区别。正本为正方体,边长各61厘米;副本则是长方体,高31厘米,竟84厘米,铭文的撰写者、书丹者与正本相同,不同的是镌刻者。后段包括清末至民国,墓志走向衰落,数量锐减,无正、副本之分,正文的书体以隶书为主,偶见楷体。
总之,上海地区墓志出现年代较晚,与中原地区墓志相比,晚了近千年。同属唐代,上海地区的墓志与中原相比却仍处于相当稚嫩的阶段。进入两宋,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南宋,随着都城的南迁,许多中原士族望姓都迁居到了上海地区,包括墓志在内的各种礼仪习俗都带到了上海地区,使其墓志数量或质量随之增加和提高,行文也趋向规范。明清两代,上海地区墓志的各个方面与中原地区完全趋同,有些甚至超过中原,很多墓志都由当时较有声望的人士所撰写。
从古代文献来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包括上海地区在内涌现出一大批文人墨客,在他们的传世文集中收藏了许多上海籍士人的墓志,可见当时墓志文化的繁荣。
[1](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第页。
[2](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第53页。
[3](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第页。
[4]墓志铭碑文网由中国古代、现代碑铭研究会主办,其为墓志铭、碑文研究、写作机构,由24名省级以上作家和9名专家教授组成。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介绍:李宏利,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wh/88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