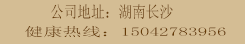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台湾著名医院过世,享年89岁。
对大家来说
让我们记住余光中老先生的恐怕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 《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这里,喵小编想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选自《故人风清:文化名人的背影》(理想国,出版)一书。
诗坛翘楚余光中
文:张昌华
1.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想起了许多事情。”余光中说他读过、写过、译过相当多的抒写火车的诗,他最喜欢的是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这一首。探究一下余光中的内心世界,抑或是那一声凄苦长啸的汽笛,唤醒了诗人绵长而沉重的记忆吧。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诗人如是说。
余光中记忆深处铁轨上的第一颗铆钉,当是九九重阳节。“谁言秋色不如春,没到重阳景自新。随分笙歌行乐处,菊花茱萸更宜人。”重九登高,两千年来绵延不绝,典出何处?据余光中考,源之《续齐谐记》中记录了一个家族为避灾祸,盛茱萸囊饮菊花酒登高的故事,一个美丽而哀怨的传说。
年的重阳节,美丽的少妇孙秀君偕同亲友攀南京栖霞山登高眺远,动了胎气,次日凌晨产一男丁。族人命名“光中”,光耀中华之意。母难,令余光中的“寸草心”终有难报“三春晖”之恨,但他很自豪自己的生日,那毕竟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余光中得意地自称为“茱萸的孩子”。
余光中,祖籍福建泉州永春人,著名的侨乡之乡。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人。在常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福建永春任教,与时任县教育局长的余超英结为伉俪。余超英后供职于民国政府专事侨务。“茱萸的孩子”生于人文荟萃的六朝胜地金陵,十代名都的灵山秀水浸润着他的豁齿童年。
然而,记忆又像铁轨那样凄冷。
往事知多少?童年的花瓣还未尽绽放,却被战争的硝烟骤然卷去。“故国不堪回首”,烙在余光中记忆中最深的印记是做亡国奴的悲哀。炮声一响,父亲旋即随机关撤往武汉。母亲携着九岁的余光中随着逃亡大军从南京城里到常州乡下,旋经陶都宜兴、太湖渔村,萍飘四处。
为避日寇追捕,他们母子或藏身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或躲在路边败垣残壁的阁楼上。绝望之中搭乘一条运麦的民船逃往上海,孰料船过鼋头渚撞上了宝丹桥,翻舟覆顶,幸大难不死,总算到了上海滩,寄居在法租界友人的屋檐下。
余光中要上学了,租界是洋人的世界,要学洋文,只靠母亲为他做英文启蒙教育。烽火三月,幸而接到万金家书。远在重庆的父亲希望他们去团聚。次年,由水路经香港,绕道越南,再由昆明辗转万里始到山城重庆。
江南少年的余光中成了川娃子,他进了由南京迁来的教会学校青年会中学。校舍是借用的破败的民宅,但他在这里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学校里的孙良骥老师,家中的二舅,把他搀引入古典文学殿堂。韩潮苏海的圣贤文章陶冶了他的身心,英文也大有长进。经一番风霜,在校内语文竞赛中,余光中脱颖而出,“光耀校中”,英文作文第一、中文作文第二、演讲第三。
战时书籍匮乏,他向一位同窗借得一本《英汉大辞典》,强闻博记,恨不得鲸吞。一次富家子弟们聚首斗阔,余光中好胜挤入“露一手”,他问谁知道一个英文单词最多有几个字母。无人敢接招。余光中一口诵出“floccinaucinihilipilification”二十九个字母,语惊四座。
那时,余光中学业偏科,考语文,他为同学捉刀;考数理,同学给他打派司。不知何因,他对地理的兴趣特浓,爱读地图,把地图当作《圣经》来读,以至形成他终身收藏地图嗜癖;同时,亦钟情天文、绘画和翻译。后来翻译了《凡·高传》,博得盛名。
国人八年浴血,终获正果。抗战胜利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归故土。年他高中毕业,同时报考北大、金陵大学,双榜题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余光中有太深的恋母情结,为依母膝,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语系。
此时,他曾受教于吕叔湘先生帐下。吕先生朴素清纯的译风使余光中受益终身;那时他还常聆听冰心、曹禺的讲演……大一的那年,余光中牛刀小试,翻译了拜伦、雪莱的诗作在报刊上发表。痛心的是内战狼烟又燃,他在金陵大学仅读一年半,复流离上海、厦门。在厦门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一次“各言其志”座谈会上,他第一次表白心迹:“我将来要当作家。”
国事蜩螗。年他滞港辍学一年。年就读台大外文系。在文风颇盛的台大,他成为黎烈文、赵丽莲、曾约农先生的高足。曾先生是曾国藩之后,他的开明与宽容,教余光中铭感五内,先生竟允许他以译文《老人与海》充作毕业论文。更令他难忘的是有幸亲炙梁实秋。
经同窗好友蔡绍班绍介,将余光中的诗作转请梁实秋圈点。梁实秋读之,觉得此后生可爱,前途无量,亲笔复信鼓励有加,同时指点迷津:“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些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
余光中受惠欣喜不胜,旋登门拜师,梁实秋一心奖掖,余光中不孚厚望终成诗文大家。这对师生之谊酝造了一曲文坛师生的佳话。是时,余光中经常向《中央日报》、《新生报》投稿,每稿必中,声誉鹊起。
大四的那年,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他恳请梁实秋作序。而梁实秋潇洒,竟以一首三段格律诗充之。余光中怏怏,斗胆上门宣泄怨绪,说先生的诗没有针对自己的集子写。梁实秋很大度,淡然一笑,说以后再写一篇书评弥补吧。梁实秋果然践诺,写书评,对余光中的诗作中旧诗的功底和对英诗营养的一并汲取的创作方法予以肯定。他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线路。”
余光中一直称梁实秋是“恩师”。他为梁实秋八十七岁华诞编了一本《秋之颂》,年梁实秋突然西去,次年梁实秋冥寿日,余光中在梁墓前,三次点火将五百七十八页《秋之颂》焚祭,祈祷恩师在天之灵。曾有评论者说余光中是“新月传人”、“新月的最后一位旗手”。此言确否,历史自有公论。但梁实秋的文风,特别是他的为人,那恢宏的气度,风趣不失仁蔼,谑谑自有分寸的儒雅风范,对余光中影响深远。
由此,余光中正式开始他的文学之旅,七十年代他如日中天,虽未达“诸葛大名垂宇宙”之望,但真正地“光耀台湾”了。
此时的记忆对余光中来说,又像火车汽笛那样昂扬、激越。
后来,余光中与友人共同创办《蓝星诗社》杂志,参与现代诗的论战;再后来他“文化充军”,三度赴美,在爱荷华大学创作班深造;拜美国当代名诗人佛洛斯特为师……一路拾级而上,春风骀荡,终成大器,光耀中华。
2.
满亭星月
余光中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年少气盛时他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人类整个文化,好一个“千手观音”。其著译林林总总排列案头,犹如风光无限,满亭星月。
透视他的生活和家庭,亦可堪称星月满亭。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位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唯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学。
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作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在他退休后仍热情挽留,作为学校的“门脸”,每遇事不遂,一打余光中牌,便无往而不胜。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他说他生就一副“不列颠的脸”,西装、领带,洋气十足,外表一本正经;但他的锦心绣口是有名的。他把谐趣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他刚到中山大学执教,他称女研究生们为“村姑”,毕业后这些女弟子们相约来为他祝寿,他对“村姑们”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说得大家笑得前仰后翻。学生们都说,把听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
他是诗文大家,一次饭桌上论道,他说菜单是诗歌,账单是散文。自己却戏言:“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又说:“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
由于他德高望重,出书索序者如过江之鲫,他一面发牢骚:“奇怪了,我又没跟人借钱,怎么一下子出这么多债务,永远都还不清呢?”一边又说“受序人像新郎,新书像新娘,写序者就是证婚人。”于是又一本正经地“证婚”:他写序,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就文本探人本,亦艺术人格。在不胜其烦中,他说真想写一篇《序你的大头》,朋友听了,抚掌大笑。
青年时期,他亦参加文坛论战,中年以后,他已无兴趣,对请邀的朋友说:“与其巩固国防,不如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晚年,他的作品仍频频获奖,他见其他领奖者都是后生,在致词时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
年,余光中应邀到四川大学讲学,有几位研究生拿出他的诗集请他签名题词。当有人指出某本书是山东某出版社盗印时,余光中幽默地说:“山东出圣人,又出响马嘛。”把幽默当作是荒谬的解药。
余光中的家庭是女性世界。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为伍,戏称余宅是“女生宿舍”,他是“舍监”……他的谐趣尽现在他的洋洋洒洒文字中,《我的四个假想敌》清淡中蕴深情,读之无不捧腹、喷饭!
关于婚姻,余光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值得玩味。
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
说来有趣,余光中与妻子范我存的结合,没有传奇色彩,但倒真正体现一种缘分。
童年时代,母亲常携余光中到常州漕溪探亲,舅家的表兄弟姐妹有三四十之多。斯文秀气的表妹们给儿时的余光中留下了美好回忆。
两家长辈曾戏说,将来让余光中娶哪个表妹吧。若干年后,余光中果真娶了表妹,不过是那一群表妹之外的一位表妹范我存。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早年留法,是浙江大学教授。母亲孙静华在上海蚕丝公司工作。他们夫妇都很“前卫”,将女儿寄在她南京的姨妈家,就读贵族学校明德女中。
范我存九岁那年,父丧。抗战胜利后,余光中回到南京,在范我存的姨妈家两人初识。少男十七,少女十四,初次相识谈不上一见钟情,但双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范我存印象最深的是听姨妈说这位表哥人品好,学习好,又会绘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初识不久,范我存便收到余光中寄来的一份同人刊物,刊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诗作。可笑的是余光中不知这位表妹的大名,在信封上写小名“范咪咪”收(此昵称延续至今)。范我存觉得有点突兀,朦胧中被表哥的文采倾倒。
年,因时局动荡,范我存回到上海。俟余光中第二次逃难到沪,欲觅这位表妹时,范我存已随亲戚飞往台湾,失之交臂。直到年,余光中一家到台,才重续旧缘。那时范我存肺病刚愈,身材颀长如水仙般袅娜飘逸;余光中元气淋漓,风华正茂。台北、中坜两地相望,有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憾。共同的志趣与爱好催发了爱情的种子。
刚开始双方家长不太欣赏此事,一个烦对方患过肺病,一个嫌对方有点书呆子气。余光中痴情,用小刀在自家枫树干上刻下“Y?L?M”(余、爱、咪三字的第一个字母),范我存也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余光中在翻译《凡·高传》时,每译一章便寄给范我存誊写,正面是译文,反面是情书。两人合作珠联璧合,十分愉悦。他们携手划桨,终将爱情之舟驶达彼岸。相恋六年之后的年,他们携手步上红地毯。梁实秋等一批社会名流是他们婚宴的座上客。
余光中与范我存结婚照
余光中追求范我存,不全因表妹温柔美丽,重要的是“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的品位,这是吸引我的特质”。遗憾的是婚后的范我存不得不淡出殿堂(文学),深入厨房,继而成了“一窝雌白鼠的妈妈”。
七年内,她成为珊珊、幼珊、佩珊、季珊四个女儿的母亲。家中八条小辫子在飞舞,范我存上奉高堂,下育儿郎,成了八口之有的掌家婆。公公生性好客,余光中交游又广,主雅客勤,访客的鞋子常在门玄关排成长龙。门铃声电话声声声入耳,小的哭大的闹不胜其烦。有时门铃电话铃齐响,范我存不得挟着孩子去开门或接电话……范我存成了余家的内务部长、外交大臣、不管部部长。
古训“子不教,父子过。”余家非也。对子女教育的重担,余光中也尽数下放给太太。“从小到大,四个女儿的学校他都没去过,老师叫什么名字他更不知道。”一次范我存打趣地问:“哎,你怎么不担心孩子的功课?”余光中倒理直气壮:“为什么要人管哪,我以前念书还不是自己念?念书本来就靠自己。”这话倒真把范我存噎住了。
外柔内刚的范我存,亲和力又特别强,里里外外她都处置得十分周到和得体。她像一株大树,为余光中撑起一片绿荫。每谈妻子,余光中十分动情:“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这些深情洋溢在余光中献给范我存的诗作《三生石》、《私语》和《珍珠项链》中的字里行间。
昔日范我存,而今“我存”何处?成了“范我无”了。范我存不是圣人,有时心中难免有点怨气:“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去挡。”范我存是“圣人”,她明白牺牲了“我”事小,得到的却是他的辉煌事大。“当然,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以他为幸,为他牺牲也值得了。”范我存是一个站在余光中后面的无名英雄。
夫唱妇随,是中国式的传统美德,夫不语,妇善为,这个境界就更上了一层了。余光中一生作诗八百余首,其中有百首是情诗。像《等你,在雨中》中的一位像“莲”的小情人,就很引人遐思,甚而,有人妄加臆测,范我存表现一种惊人的理智与大度。她说:“有些情诗不一定写实,何必认真研究?有很多事情最好别追根究底。”话中充满着理智、宽容,更多的是自信。
余光中十分欣赏太太见怪不惊,大而化之的美德,压根不去从字里行间搜寻微言大义。否则,余光中岂能“光中”?余光中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礼赞他的太太:“她的优点很多。”“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我们能契合,而且她能充分和我的事业、我的朋友融成一片。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又有共同的朋友,婚姻怎么不稳固呢。”结缡四十多年,他们相敬如宾,夫妇好合,如鼓琴瑟。
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余光中的四个女儿中有两位博士,另两位也学有所成,早羽翼丰满翱翔在自己的天空。她们在人品与文品上都秉承了父母,文雅而又有棱角。她们都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的潜质,都是舞墨的好手,但他们却很少写文章。余光中埋怨“她们大都懒于动笔”,而女儿们却振振有词:“我们怎么也写不过爸爸了,所以干脆不写。”
从女性的角度,林海音对余光中有个十分中肯的评价:“没有像光中这么好的丈夫了。”而朋友痖弦说得更酷:“我还真希望他也有点缺点呢!”
岁月不居。如今星星已不是那个星星,她们星罗棋布在世界各地;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白发与皱折使其黯然几许;但在范我存的心中,他们家的太阳仍是那个太阳——不老的余光中。
余光中、范我存伉俪,一对终身最佳“牵手”。
余光中一家
3.
望乡的牧神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
余光中以这首“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乡愁》,一夜间令千万大陆读者倾倒。他这位“望乡的牧神”在阔别近半个世纪后,才独自擎着“一把怀古的黑伞,撑着清明寒雨霏霏”回到故土。不过,自那以后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
辛巳年重阳节时分,余光中应邀随江苏籍台湾作家代表团回乡采风。他再次踏上魂牵梦绕的故乡土地,屐痕处处,访问了南京、扬州、苏州、无锡,特地在故里常州独自作了短暂的逗留,所到之处受到的礼遇和欢迎是空前的。唯有门前旧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在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在南京出生,九岁才离开南京到四川读中学,后来又回到南京读大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这十二年的积累使我成为一名有思想的二十一岁的青年。”
“我是台湾作家,我也是南京作家,也可以说是福建作家,其实我最想说的是‘我是中国作家’!”他在谈两岸诗歌创作时,还诚恳地说,“他乡之石,可以攻玉,故乡之石,可以攻错”。南京大学是他的母校,为母校明年的百年华诞,他专门写了七千字的长文祝贺。他渴望参加这一盛典。他目睹了南京的巨变后说:“刘禹锡曾写过‘金陵王气黯然收’,而我看到的南京是‘南京勃然新’。”他说他想到夫子庙、长江边独自走一走,在故乡的怀抱里沉思默想之后,写点东西出来。
“蛟龙东去欲探海,崇楼北望可阅江”。当他登上下关狮子山新建的阅江楼时,更是感慨万千:“我们登阅江楼,感觉气象非凡,长江天堑可以克服,海峡两岸的关系也一定可以。”
余光中与江苏的学者、诗人、作家们讨论诗歌创作时,对读者反映当前有的诗歌太晦涩看不懂时,他表示忧虑和小孩白癜风可以治好吗治疗白癜风什么药好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wh/8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