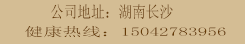利维坦按:这篇文章的确让我重新认识了硬核——“硬核一边关心着如何‘操翻这个世界’,同时一边又有着相反的观念:尊重别人。”或许这种矛盾的结合体才是硬核激荡失真回授的核心理念。和那些大牌的、在商业上极为成功的摇滚乐队不同,硬核粗糙,原始,激进,不关心流行和商业,更重要的是,它的魅力来自于现场而非录音棚,风车臂的SlamDancing(Moshing)既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同时也消弭了乐队(台上)和歌迷(台下)的界限。简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典范。
如今,当年纽约硬核的那一帮人都已步入中年,昔日的演出场地也已纷纷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化”的部分图景,扑面而来的商业之花到处盛开。但这股地下的暗流一直在涌动着,因为它往往并不单纯意味着是一种音乐,而是一种随时都会爆发的强力能量。
文MichaelStahl
译/皮卡丘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narrative.ly/the-last-time-new-york-was-hardcore/
上世纪整个90年代,一种能量爆棚的地下音乐社群不顾一切地通过强力和弦、碰撞舞和舞台跳水,顽固地操持着它的反叛根源。硬核到底发生过什么?
译者按:碰撞舞/SlamDancing也被称作Moshing,这是一种在比较激进的音乐演出现场的观众进行的互相碰撞推搡的舞蹈形式——比如硬核朋克以及某些极端金属现场,尤其是激流金属(ThrashMetal)。这种舞蹈形式最初来源于硬核朋克(HardcorePunk)和脏摇滚(Grunge)。从80年代末期开始,碰撞舞从Grunge等另类风格的演出现场集体行为变成了一种更流行的模仿来的娱乐活动。人们在观看现场演出的时候跳碰撞舞,甚至在听录音专辑的时候也跳碰撞舞。而在硬核社群里的Mosh有着更独特的文化意义和仪式感,它代表着一种硬碰硬的真实感和互相激荡又彼此照顾的社团文化。
注:文中黑体为乐队和厂牌名称,斜体为专辑、歌曲或者影片名称,红字为译者补充和有疑问的部分。
失序的愿景(VisionofDisorder)于年在纽约市翠贝卡区湿地保护区的演出照片。基斯·维克(KeithWick)摄我被人群严严实实地裹住了,曼哈顿西18街的罗克西俱乐部(Roxynightclub)此刻已经挤满了超过人。这里非常热。我们已经不知道跳了多久的舞。然而,那些大弧度旋转的风车臂和像标枪一样被抛掷出来的身体,在这样一个年的夜晚,与罗克西早年滑轮迪斯科舞(RollerDisco)那些被抑制的动作已经相去甚远。此外,我们还对这些为了承受下落的力量而专门改造过的俱乐部地面和墙面心存感激。
迪斯科时代的超短裤和长筒舞靴消失了,来看演出的为数不多的姑娘们大都穿着工装短裤和马丁大夫靴。而汉子们都扒光了衣服展示着他们光鲜的纹身和乳头环,以此来搭配他们酷酷的鼻环再合适不过了。
室内的灯光被调暗了。各种身体穿刺环和钉碰撞回授着,盖过了人群的吼叫声。鼓手快速敲打了四下鼓棒,混乱开始了。
灯光重新开始闪耀。热门乐队受够了(SickofItAll)的主唱娄·寇勒(LouKoller)出现在舞台前方,一堆粉丝簇拥在他的脚边。
他喊出了第一句歌词:“想想我们曾经拥有过什么!”
观众们接着补出了下一句:“喔——噢!”
在一段朗朗上口的乐句之后失真的吉他声爆裂开来。人们必须自我保护,以免被那些像被鬼上身了似的跳着碰撞舞的人撞伤。寇勒把麦克风递给一位人潮冲浪者(crowdsurfer,摇滚演出现场中从舞台上跳到人群中,或者从人群中跳到人群上方,被其他观众用双手托起来在人群上方冲浪的人)。舞圈(原文中是pit,指的是moshpit,即跳着碰撞舞的人围起来的圈)中有人跌倒,有三个人迅速将其扶起。
“硬核非常真实,”凯文·吉尔(KevinGill)说,他曾是地下硬核唱片厂牌为团结而努力(StrivingforTogetherness)的负责人之一。“朋克的态度可能是一边挤一边对你喊着,‘哥们,怎么样?’,而硬核则是直接一拳干在你脸上。硬核一边关心着如何‘操翻这个世界’,同时一边又有着相反的观念:尊重别人。”
在数分钟的几乎完全爆表的感知轰炸后,乐队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人群欢呼雀跃的同时已经在为即将到来的下一首歌做准备了。
硬核大约是在40年前开始了它在地下音乐界的统治,它强烈、原创并且创制出一套极具传播力的文化气氛。尽管在今天硬核音乐的编织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音乐厂牌的范畴,然而在它初现的70年代末期,硬核仅意味着一种更喧闹、快节奏的朋克摇滚形式。到80年代,在与激流金属融合之后,它又经历了一番起起落落。在整个90年代,一批批新浮现的面孔主导了一场与朋克、金属、嘻哈音乐(Hip-hop)的混合联姻,硬核之火被反复重新点燃,在纽约市内区及周边地区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最高峰。
“90年代中期是最棒的,”长岛乐队失序的愿景的发言人蒂姆·威廉姆斯(TimWilliams)如是说。“(在这种音乐中)没有矫饰,没有包装,没有激光秀。这种音乐来自一个真诚的地方,我与这些人都交情颇深。他们从不说屁话。”
***
在《纽约客》杂志年一篇关于纽约硬核的文章中,科勒法·沙奈(KelefaSanneh)写道,“这是一种带着与生俱来的双重否定的音乐类型:用反叛对抗反叛。早期的朋克们认为摇滚乐已经走上了歧路……但是当朋克也不给力了以后,硬核小子们的时代就来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让前辈们难堪。他们的想法就是用比朋克更朋克的方式淘汰朋克。”
大约在年,纽约下东区的硬核风潮崛起之前,洛杉矶和华盛顿首府冒出了一堆硬核乐队。A7俱乐部位于第七街街角污秽的A大街,它是第一家将硬核演出常规化的俱乐部。诸如不可知论前沿(AgnosticFront)、警报之因(CauseforAlarm)、墨菲的法则(Murphy’sLaw)、解毒剂(Antidote)、德国佬(Kraut)等本土乐队被邀请到了这间俱乐部那狭小的、铺着厨房地砖的休息室去,与歌迷们一起跳碰撞舞,一起唱。早期和他们一起玩的不过就几十人,主要是年纪大点的青少年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压低重心,甩着臂膀互相撞击,他们托起人潮冲浪者,并为玩舞台跳水的人组织起人肉垫子。他们看起来就像严阵以待的橄榄球队员,穿着破损程度不同的制服,而且既没有球也没有可供判读的球门。托尼·拉特曼(TonyRettman)关于80年代纽约硬核(NYHC,NewYorkHardcore)的口述史文献中提到这些早期参与者时,说他们“全都是有精神问题的人,而且全都住在大街上”。
年11月12日不可知论前沿的乐迷正在位于曼哈顿下东区的A7俱乐部一边看乐队演出一边跳着碰撞舞。杰西卡·巴德(JessicaBard)摄,德鲁·斯通(DrewStone)提供图片
这帮人的混合音轨包含了一些速度快过史上任何摇滚的曲目,其间充斥着反体制的歌词和呼吁社会觉知以及个人自我觉醒的意象。有时,乐队甚至不按正确的方式表演曲目。吉他和主唱的设备线缆似乎总在出问题,但这些都不重要。这种在狭小空间中释放出来的侵略性音乐极具俘获力,没人会停下来享受轻松时光。
外地来的那些后来很有名的硬核乐队,诸如黑旗(BlackFlag)和坏脑(BadBrain)也曾受到A7乐迷的热捧。在加入嘻哈元素之前的野兽男孩(BeastieBoys)早期也曾在这个俱乐部初试牛刀。在8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鲍威利(Bowery)区的CBGB、东十一街的利兹(Ritz)以及其他一些曼哈顿俱乐部开始预约硬核演出。
也大约在那个时代,皇后区白石镇(Whitestone)长大的凯文·吉尔“一头栽了进去”。
“硬核是不假修饰的真实,”这位现年44岁、非常乐观、高个且几近光头的前唱片厂牌经营者补充道,“他们都是有着普遍问题的普通人。”
正如许多纽约硬核乐迷一样——包括我自己——吉尔一开始接触的是重金属。“从炭疽热(Anthrax)和金属(Metallica)乐队到受够了(SickofItAll)、消磨时间(KillingTime)、掠夺者(Merauder)以及其他一些80年代的硬核乐队只经过了很短的一段历程,”吉尔在接受了一些高中校友推荐的录音拷贝之后开始着迷于这种重型音乐。
克雷格·塞塔瑞(CraigSetari),受够了(SickofItAll)的贝斯手(译者勘误:原文中说是不可知论前沿,应该是打错了),年与乐队在新泽西演出。(照片由克雷格·塞塔瑞提供)
随着局面的不断扩大,到了这个十年的末期(80年代末),市区里的这些俱乐部老板们越来越不愿意去对付那些日渐增长的暴力事件,因为碰撞舞、跳水等其他乱七八糟行为导致的观众受伤,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纠纷。知名硬核乐队诱因缺失(WithoutaCause)和华氏度(Fehrenheit)的成员莱尼·贝德纳兹(LennyBednarz)回忆,他曾经见过两个来参加演唱会的人在一场演出中一边挥舞着满满一袜子的电池,一边加入了一个碰撞舞圈。他又补充说,“那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在俱乐部里喷梅斯喷雾(Mace,自卫辣椒水喷雾)”。亚瑟·斯密琉斯(ArthurSmilios)是80年代晚期大猩猩饼干(GorillaBiscuits)乐队的一名成员,他说,他注意到那个年代有一种“帮派意识(GangMentality)”正在凝结,这种意识演变到后来在CBGB甚至频繁出现的大规模斗殴事件,最后这间著名的俱乐部也不得不把每周末的日场硬核演出停掉。斯密琉斯认为那段日子真是纽约硬核的“低谷期”,许多常规演出都被取消了。“情况不再有趣,”他补充道。斯密琉斯离开了大猩猩饼干,一部分是因为他想去读一个大学学位,另一部分是因硬核界肮脏的变化。
由于各种小俱乐部都不再对硬核开放了,或者有些就干脆直接倒闭了,比如A7俱乐部就在年关张。吉尔说“这些乐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他与许多其他硬核粉丝们却有机会接触到了另一种新的硬核,那个时候这种音乐会吸引到更多的爱好者。
***
一些独立纽约硬核乐队继续艰难地维持着,到处找地方演出。他们开始将由老派朋克(old-schoolpunk)发展出来的硬核与激流金属和嘻哈音乐结合,打造出了一种响彻地下的新声音。他们最经常演出的地方是位于下东区,离原来的A7俱乐部旧址仅仅相距几个街区的邦德街咖啡馆(BondStreetCafe)。“就是那个地方,”吉尔回忆道,“那地方就像是城墙上的一道裂缝。”“那几乎算不上一个演出场所,”他继续说道,“但这还是令人振奋的。在那个年代,曼哈顿哪还有几个正经的演出空间愿意让一帮疯子在演出之前站在台前一边抽烟喝酒,然后再闹上三个小时震得你屎尿失禁?”
“邦德街那些演出,让人会有被电击一般强烈的情绪,”前任封闭(Shutdown)乐队主唱马克·司孔度托(MarkScondotto)说。他在青春期早期身高就有五尺二,经常陪着哥哥到俱乐部去,而他哥哥则保护他不受那多个跳着碰撞舞和玩舞台跳水的恶棍伤害。“你走出那些地方的时候,就感觉你像是穿着溜冰鞋一样。那些碰撞舞圈真是相当吓人。”硬核的主要吸引力并非来自音乐,而是那些演出的氛围,最典型的格局就是那种乐队离观众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超小型俱乐部:
“这种歌手把麦克风交给观众,以及人们跳上舞台的想法……非常令人震惊,”拍摄了讲述90年代中期硬核音乐文化的纪录片《纽约硬核》(NYHC)”的导演弗兰克·帕维奇(FrankPavich)说。“这就像摘下那闪亮的超级摇滚巨星,然后将其降格,直至他们成为我们之一,而我们也成为他们之一。”
“我并没有任何演奏乐器的能力,然而如果谁给了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感到我似乎获得了某种能力。它让我感到我成了乐队成员之一,”44岁的维吉尼亚·克雷斯(VirginiaKress)说。在20多岁的时候,她曾是那些纽约硬核演出现场中女性常客中的一员。“这就像一次觉醒。”
一次90年代末期在下东区的地下顶点(AcmeUnderground)演出空间的纽约硬核演出商凯文·吉尔在为摔跤手渡鸦(Raven)做宣传——在他T恤上的图案(照片由凯文·吉尔提供)
我也像是被牵引光束给带到这个世界里的,一个来自阿斯托利亚(俄勒冈州西北端的城市)的焦虑满满的青少年,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突然第一次感到自己似乎融入了某个社群,甚至是一种运动。所有这些体验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8美元的花费而已。
吉尔说,硬核演出替他“灭掉了那些普通货色”。如今,作为一位旧金山居民,他会为了要花费75美元去看一场在座的沃菲尔德剧院举办的像杀手(Slayer)这样成功的金属乐队的演出而感到心疼。“我几乎希望自己从没有去看过那些硬核演出,”他说。
到了年末,更多的俱乐部开始为硬核演出的举办提供空间,这其中包括也坐落于下东区的布朗尼俱乐部(Brownies),以及穿过城镇在翠贝卡区的湿地保护区俱乐部(TheWetlandPreserve)。CBGB又一次重新开始在周日举办日场纽约硬核演出了,尽管邦德街咖啡馆在年就不巧倒闭了,位于圣·马克斯广场拥有邦德街咖啡馆两倍容纳量的科尼岛高潮(ConeyIslandHigh)俱乐部随后填补了前者的空缺。
90年代曼哈顿市区是硬核的活动中心,然而这种音乐的影响力扩散到了外部区域,长岛、新泽西、上纽约州、康涅狄格甚至更远的地方,在更多俱乐部繁荣的区域孕育出了小范围的硬核文化。我在皇后区科洛纳北大街(NorthernBoulevardinCorona)的“高城”(CastleHeights)做了三年的音效师,那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个社区相当有知名度的凯文·卡斯特(KevinCastle)说,“我们有自己的圈子”。他是封闭乐队的马克·司孔度托的哥哥,现年48岁的他已经在高城做了10年的演出预约员。“在、年我们大约每周能举办三四场硬核演出。我们办的演出远远不够,因为乐队实在太多了。”
唱片厂牌也来了。布鲁克林硬核乐队生化危机(Biohazard)在年通过走鹃唱片(RoadrunnerRecords)公司发布了专辑《都市规则》(UrbanDiscipline),走鹃唱片是一家签约许多纽约硬核乐队的独立唱片厂牌。生化危机的专辑在世界范围内卖出了万份的拷贝,他们的音乐录影《惩罚》(Punishment)成了MTV深夜档节目“甩头党的舞会(Headbanger’sBall)”中有史以来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录影——硬核文化中许多最著名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这部音乐录影中,录影中乐队表演这首曲目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一起疯狂。
生化危机(Biohazard)的音乐录影《惩罚》(Punishment):
“突然之间,人们看到了这部音乐录影并开始发出‘哇喔,纽约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这部音乐录影的制作人德鲁·斯通(DrewStone)说。“所有看到这部音乐录影的纽约小孩都在想,‘我也得组一支乐队。’”
年,凯文·吉尔成了一家总部在德国的小规模唱片厂牌为团结而努力(StrivingforTogetherness,缩写为SFT)的美国经销商。许多年以前,他是一支来自曼哈顿上东区的名不见经传的重型乐队诱因缺失的好朋友。“他们拥有最烂的演出,”吉尔说,“我记得他们演奏起来就像一家中国餐馆之类的鬼东西。”他到处为诱因缺失的一张唱片小样寻找代理商,“两三家唱片厂牌的反应是‘谢谢,但还是谢谢了。’”之后,他用尽了模仿德国人口音的能事,吉尔回忆SFT的老板给他发来了回音:“好,这些东西灰强棒(原文sah-lid,疑为带口音的solid)。也许我们可以先做一张七英寸唱片。”
年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NoRedeemingSocialValue)乐队的成员摆拍的照片。上排,从左到右:主唱:麦克·迪克森(MikeDixon)、吉他手肯特·米勒(KentMiller)、鼓手维尼·魏略(VinnieValue);下排,从左到右:歌手迪恩·米勒(DeanMiller)、贝斯手麦克·“小孩”·帕尔默(Mike“TheKid”Palmer)。照片由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提供。
随着硬核文化的复苏,吉尔成了那些初露头角的新乐队寻找东家一定要去拜访的人物。这其中包括来自长岛的失序的愿景,主唱蒂姆·威廉姆斯拥有一副在慵懒绵长与原始尖叫之间回荡的嗓音。诱因缺失解散之后,部分成员组成了华氏度乐队,新乐队将嘻哈、硬核和氛围摇滚乐结合在一起。90年代纽约硬核的首支派对乐队就是来自皇后区的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他们的七英寸唱片《硬核掉你的屁股》(HardcoreYourLousyAssOff),唱片封面展示着主唱迪恩·米勒赤裸的屁股,屁股上是他弟弟吉他手肯特用黑色记号笔写下的“HARDCORE”(硬核)。
“演奏优秀的音乐是一回事,而引人发笑就完全是另一件事了,”现年39岁的肯特·米勒说。唱着关于难以想象的超大瓶麦芽酒的歌——“新64(New64)”(64指的是64盎司瓶装麦芽酒),看着全校最可爱的妞和白痴约会——“你男朋友是个圭多(Guido,这是挖苦意大利裔美国工人阶级古怪衣着和行为风格的一个词),”米勒兄弟坦承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乐队虽然现在还时不时有演出,但他们却不是一群有才华的音乐家。乐队的唯一且真实的目标,如其所称,是要始终确保“来看演出的人能度过一段好时光”。
“我们把能抓到手的一切都抛向观众,”45岁的迪恩·米勒回忆着,接着他列举出一大串他曾经抛向观众的物品,其中包括五彩纸屑、钱、大红肠和躺椅。“有一次我们告诉观众,我们只剩下七英寸唱片和……和鱼,”肯特回忆说,“你们要哪个?‘鱼!’于是我们把鱼抛向他们。”后来迪恩说,到了那天夜里演出结束之后,俱乐部到处都分散着鱼的残渣,那些掉落在游戏机下面和其他一些角落里的鱼渣第二天全都腐烂了。
他听说第二天轮到不可知论前沿在同一个空间演出,“硬核教父”维尼·斯蒂格玛(VinnieStigma)演到一半时很大声地问为什么他总是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迪恩回忆道:“后来有人告诉他,‘昨晚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在这里演出,并且往观众席抛出了一条鱼,’他说,‘哦,难怪了。’”这支乐队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习惯,就是裸体表演。有一次他们去德国演出,主办方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再一次裸体演出就将得到一份额外的奖金红利。迪恩的回答是,“我们愿意免费这么干,但是如果你要给我们额外的钱,我们当然更乐意不过了。”
左图:莱尼·贝德纳兹正在展示一张90年代经典的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的贴纸;中图:歌手迪恩·米勒举着一张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的密纹唱片;右图:迪恩正在翻看维吉尼亚·克雷斯收藏的NYHC纪念品。这些照片是上个月在曼哈顿下东区邦德街咖啡馆的旧址之前拍摄的,贝德纳兹和米勒曾经在这里演出,而克雷斯也常去那里看演出。所有当今的新照片由卡洛斯·迪特雷(CarlosDetres)提供
硬核后来也分裂成了许多难以置信的类别,其中包括“死核(deathcore)”,一种结合了死亡金属和硬核的音乐类型);“噪核(noisecore)”,一种结合了尖叫的人声与嘶嘶声的硬核,由于这种音乐扭曲得厉害,以至于旋律都变得无法辨识;除此之外,“后硬核(post-hardcore)”运动带来了更成熟且不那么激进的创作风格。布鲁克林乐队寄生鲶(Candiria)奇迹般地将许多不同风格的重金属与嘻哈、爵士、迷幻摇滚以及其他一些风格混合在一起,他们的音乐有时甚至带着拉美或非洲风格的重拍。狗咬狗(DogEatDog)则是通过直白的说唱歌词结合传统摇滚配器,再加一支锦上添花的萨克斯风获得了享誉海外的知名度。丹尼·迪亚波罗(DannyDiablo),90年代在台上使用艺名伊萨克大人(LordEzec),荆冠(CrownofThornz)乐队的发言人,根据他的说法,他们的风格就像是“黑色安息日(BlackSabbath)遇上了冲刺(Rush)同时又混合了克罗马农人(Cro-Mags)”。与此同时,老派的受够了发表了充满历史感的黑胶版唱片,贝斯手克雷格·赛塔瑞将其描述为一条更“黑”的边。他们甚至与纽约的传奇M.C.KRS-ONE同场演出。
CIV,是一支纽约硬核的超级组合,它的三位成员来自大猩猩饼干——安东尼·西瓦尔里(AnthonyCivarelli)、山姆·西格勒(SamSiegler)和亚瑟·斯密琉斯(ArthurSmilios),以及流沙(Quicksand)乐队的吉他手查理·加里加(CharlieGarriga),这个组合意外形成于年。“CIV完全是一个异类,”斯密琉斯说,硬核老手瓦尔特·施雷菲尔斯(WalterSchreifels)在与流沙一起巡演的时候写了一首很活泼、有趣、类似游戏的歌《一分钟也等不了》以及另外一首《你也有份吗,布鲁图》(EtTuBruté),他希望西瓦尔里能找些人一起录这两首歌,并把这两轨录进一张七英寸密纹唱片。西瓦尔里当时作为一家纹身店老板生活在长岛,施雷菲尔斯好说歹说并且向他保证整个计划包括制作一张唱片,他这才同意。
这张单曲碟发布之后,这个团体的一位朋友——年轻导演马科斯·西耶加(MarcosSiega)希望能拍一部影像作为简历的一部分——通过这部《一分钟也等不了》的音乐录影,CIV被卖了出去。在这部录影中,西瓦尔里装扮成像杰里·斯普林格(JerrySpringer)一样的脱口秀主持人,同时对口型唱了这支歌。
这支音乐录影很快被流沙的经纪人看到,并且对它很满意。斯密琉斯回忆道:“突然之间,一场由唱片公司与一支不存在的乐队之间的较劲开始了。”
CIV录制了一张带有大西洋唱片(AtlanticRecord)岩浆印记(Lavaimprint)的专辑设定你的目标,而那支《一分钟也等不了》成了MTV频道的热播曲目。“到CIV开始演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唱片并且和大厂牌签了约”,斯密琉斯说。“这真的很古怪。”
***
我第一次去看纽约硬核的演出是在年,那时候我已经热爱这种音乐有一年半了。那时我最喜欢的乐队是当时非常热门的疯球(Madball)。我记得和朋友一起到了演出地点——哈德森大街(HudsonStreet)的湿地保护区(WetlandsPreserve)俱乐部,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看到乐队的主唱弗莱迪·克莱西恩(FreddyCricien)正站在人行道边上和乐迷以及他的朋友们聊天,离我只有几英尺。那个夜晚也是我第一次得见真正的纽约硬核碰撞舞圈,那与我在MTV电视台看到的在那些诸如声音花园(SoundGarden)、涅槃(Nirvana)、珍珠酱(PearlJam)之类脏摇滚演出现场的碰撞舞有很大差距。在那些演唱会现场,歌迷们不过就是温和地上蹿下跳。而在这个现场,据他们回忆,一开始看到那些硬核舞者很是吓人,而且他们还升级了碰撞舞,随着节拍还往舞蹈里面加入了不少太极拳和空手道的动作。但是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没有人会受伤;我看到的全是开心的笑容,每首歌过后都是掌声雷动,这掌声既是为乐队鼓的也是为那些踩点比较到位的舞者鼓的。没过多久,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也为自己愿意冒着受伤的危险而感到震惊。
“硬核并不是最棒的音乐,但是它的能量无可比拟,”那时候我很喜欢的另一支乐队荆冠的前任成员丹尼·迪亚波罗说。丹尼的纹身多到几乎只剩下眼睑是干净的了,他现在是一位嘻哈歌手,他说硬核的根源来自于那些恢复力极强的城市居民,“他们直面一切事物,”他补充道,“所以它不叫‘软核’。”
上图:90年代中期,丹尼·迪亚波罗,也就是伊萨克大人(中心位置,手持麦克风)正与荆冠乐队一起在科尼岛高潮(ConeyIslandHigh)俱乐部演出。摄影:丹·佩尔兹(DanPeltz)照片来源:德鲁·斯通(DrewStone)。下图:年,吉他手莱尼·贝德纳兹与华氏度在科尼岛高潮俱乐部演出。摄影:米歇尔·拉戈(MicheleLago)照片来源:莱尼·贝德纳兹
几乎没什么人能像纪录片《纽约硬核》的导演弗兰克·帕维奇那样将这股社会思潮具体化。弗兰克来自皇后区的道格拉斯顿(Douglaston)街区,这个街区有著名的高尔夫课程以及不断蔓延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地产生意。帕维奇现年43岁,他记得自己在年遇到了“一个古怪、个高且瘦的风趣男子”,那名男子就是凯文·吉尔,后者给了帕维奇许多纽约硬核的混录磁带,那时候帕维奇还只是个高三学生。用帕维奇的话讲,吉尔“让他扩展了眼界,见识到了另一个世界”。
四年之后,帕维奇,这位谈吐优雅的眼镜男,克罗地亚人的孩子,决定去拍摄一部关于硬核社群的纪录片。据他自己说,这部片子“完全打败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后者是由佩妮洛普·斯菲里斯(PenelopeSpheeris)导演的一部关于80年代早期洛杉矶朋克圈子的影片。
后来帕维奇承认,他并不清楚自己当初是要干什么。他招募了一位40多岁的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对硬核的概念可谓一无所知。尽管这位摄影师对纽约地下音乐知之甚少,但是他对拍摄设备却很在行,而且拥有许多不错的设备,包括一台价值10万美元的Betacam摄像机,他平时主要靠这台机器来拍新闻故事的。帕维奇的付款方式是“酬劳,拷贝,补贴”——影片拍摄的酬劳,影片的一份拷贝以及补贴性的工作餐。帕维奇还帮助保护摄相机不受围观人群以及那些从各个角度蹦出来的表演者的伤害。
弗兰克·帕维奇的《纽约硬核》纪录片截屏,拍摄于年夏天。按顺时针顺序从左上方开始:第九区的凯撒·拉米雷兹(CesarRamirez);为团结而努力唱片的凯文·吉尔;荆冠的丹尼·迪亚波罗,亦即伊萨克大人;疯球的弗雷迪·克莱西恩(弗兰克·帕维奇授权图片使用)
在年夏天,帕维奇拍下了将近44小时的采访以及跨越两周的表演。“我之前从没有做过任何剪辑,所以那次剪那部片子花了我很多时间,”他说。“剪辑的方式也是非常老派的,从磁带到磁带。”这也平添了不少麻烦,那台古老的剪辑机每个礼拜都会崩溃一次。
这部全长90分钟的电影直到年才发布。“这部电影并不是人人都能看的,”他说,“但它被拍出来了,而且我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也仍然爱着那些乐队以及所有和这部片子有关系的人。”
通过这次实践帕维奇知道了在拍电影的时候“什么该做以及什么不该做”,他的第二部正常片场的纪录片,《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发行于年,这部片子入围了奥斯卡。
弗兰克·帕维奇的第二部纪录片《佐杜洛夫斯基的沙丘》
帕维奇《纽约硬核》中最特别的部分是对维吉尼亚·克雷斯的采访,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中引用了她的话,“我不希望到了40岁还有什么人生遗憾。”那时候她23岁,一头金发,脸上打了三个洞,在采访中,她时常显得因羞涩而闪烁其词。展示完那藏在下唇内侧的纹身“SUFFER”(忍受)之后,她很害羞地笑笑说,“这是VOD(失序的愿景)的一支歌。我的最爱。”
今天的她是一位友善的家庭妇女,她在40岁生日之前六个月生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我没错过太多,”她很自信地说。“我觉得我的20岁和30岁都过得很精彩。”
克雷斯说,在90年代她大约平均每周参加三次硬核演出,既是被音乐吸引,也是被演出现场那种“家庭氛围”给吸引了。“因为我总是去看演出,所以我几乎认识乐队里的每一个人,”她说。她又补充道,她后来决定跳过大学,这样她就可以买一辆车,去其他州看演出。
“现在回想自己当初也许做了错误的决定,”克雷斯说完笑了笑。“可事实上,并没有,我并不后悔。我必须老实说。”
维吉尼亚·克雷斯(近照)在曼哈顿下东区遛儿子并炫耀嘴上的旧纹身。
即便是开车到诸如新奥尔良或者底特律这样遥远的地方去看演出,克雷斯也总能碰上,或者说撞见那些友善的面孔。于是她在每场硬核演出总能找到家的感觉。
“一旦你找到了小小的硬核圈子,你就找到了你的兄弟,”第九区(District9)的前任吉他手凯撒·拉米雷兹(CesarRamirez)说,第九区是一个来自社会经济地位变化了的南布朗克斯区的乐队。“你们互相照顾,并且什么事都一起做。”
现年39岁的拉米雷兹,曾经在邻近的一家音乐商店尝试加入第九区做贝斯手。在一次失败的尝试后,他开始努力学习乐器。一年后,在15岁的时候,他从一堆报名要加入乐队的人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后,第九区成了圈子里比较特别的一支乐队。第九区并不喜欢带上乐器坐地铁到曼哈顿区或其他地方演出,而更喜欢在布朗克斯区直接就玩大了。“我们在努力试图将灵魂塞到这坨屎中,”在谈到乐队风格时拉米雷兹说,我们将金属和硬核朋克结合在一起,偶尔玩玩爵士,写着押韵的歌词,这些歌词几乎是可以和那个年代流行的黑帮说唱歌词互换的。
拉米雷兹回忆道,有一天晚上第九区要旅行90分钟到布朗克斯北边的纽约州新帕尔茨区去演出。他说,那天这帮人,包括他自己都在整夜抽大麻、喝啤酒。乐队主唱,麦克·里维拉(MykeRivera)回忆说他们那天还集体吃了致幻蘑菇。但是拉米雷兹是唯一一个第二天还要去学校报到的人。“那天真是太疯狂了,但很有趣,”他说。
七月,第九区的前任吉他手凯撒·拉米雷兹正在圣马可广场的科尼岛高潮旧址闲逛。
正如摇滚历史里的其他时代,在硬核圈里也流行谈论自己的受害经历,包括拉米雷兹多嘴且壮实的队友里维拉。他在《纽约硬核》里笑着讲述了他自己在南布朗克斯那充满麻烦的童年故事。比如,他的母亲曾经用一把头上绑着铁丝衣架的扫帚“将他打到发烧”。
去年五月,我致电里维拉要做个采访。他同意了,他跟我讲了他的酒鬼父亲的故事——“他是那种在早上七点就要喝五毛钱啤酒的人”——而他母亲是一个“标准的吉娃娃州波多黎各野蛮人”,他还是很想念母亲的,当时他正遇到可卡因问题。里维拉一开始说希望可以推迟我们的交流,因为当时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他抱怨说胸部感觉很冷。后来我才得知,那时他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医院。“我的身体你在告诉我,‘你完蛋了,臭狗’,”后来他感觉好点儿的时候说道。
七月,他告诉我他正准备去帕萨迪那一家戒毒所进行一次为期30天的节制生活。上周末,他告诉我他已经搬回去和老婆孩子一起住了,现在他已经干净、清醒了,并且参与了一套十二步骤的戒毒项目。
***
年4月在罗克西俱乐部,我和我的朋友们聚集在俱乐部后台附近,当时受够了正在进行返场演出(encore)。整晚,俱乐部都充满狂欢、激情和骄傲的气氛。这是纽约硬核该有的,但这也算是圈子里我们所目睹过的最大规模的演出了。乐队接受了MTV新闻记者科特·劳德(KurtLoder)的采访,当时俱乐部里挤满了三千乐迷——乐队贝斯手克雷格·赛塔瑞后来在今年春天告诉我,“这是受够了乐队在纽约生涯中的最高水准”。
但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发生了,一位穿着白色吊带上衣的年轻娇小的女性突然对着一位肌肉男大喊,“你打了我,蠢货!”
这个男的举起双手,左右顾盼了一下与他同来的两个同样强壮、汗淋淋的赤膊男伴,回问道:“你叫我什么来着?”
“蠢货!”
这个男人举起右拳打在那个女孩脸部中央,一记重拳将其放倒。
场面一片混乱,分不清谁在人群里干架谁在劝架,我和我朋友们赶紧撤离了现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过程中,我对塞塔瑞说了这个故事,他的脸上很快浮现出一幅痛苦的表情。
“为什么有人会干那样的事?”他说。
尽管那夜我并没有太在意,但是那次事件无疑是硬核后来再次出问题的一个预兆。
***
“任何社会运动都伴随着衰退和流变,”曼哈顿本地电影制作人德鲁·斯通说,“硬核也一样。”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新金属(nu-metal)”控制了美国摇滚版图。硬核圈里许多人将其看做一个他们所喜爱的原味音乐的香草味版本——或者,就如弗兰克·帕维奇那样,将其看做一个“杂交”的品种。然而只有少数歌迷知道,在这段时间火起来的乐队,如科恩(Korn)、软饼干(LimpBizkit)、污点(Staind)、蟑螂老爸(PapaRoach)和林肯公园(LinkinPark)等乐队都曾受到过90年代那些引领地下硬核之声的先锋艺术家的启发。
正在创作另一部关于硬核文化的纪录电影的斯通说,“坏脑踢坏了很多门,生化危机也踢坏了很多门。但正是穿过了这些门的乐队获得了殊荣。”
上图:年7月31日,解毒剂乐队正在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Williamsburg)街区的大胜利(GrandVictory)俱乐部最后的纽约硬核演出表演。下图:解毒剂的成员在演出前在大胜利俱乐部门口拍的集体照(从左到右依次是),鼓手REA,吉他手南兹奥(Nunzio),主唱德鲁·斯通,贝斯手特里斯坦·麦克(TristanMichael)。
同时,90年代早期激发硬核重生的因素到了90年代末期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科尼岛高潮于年关闭,在经营了小四年多之后,业主因为无力再支付房租只能关门。同一座建筑里一间平方尺重新修葺过的公寓房租金是.3万美元。
一位不动产开发商买下了湿地保护区俱乐部所在的建筑,在俱乐部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一批极高端的公寓落成了。从此,那栋建筑的租客都变为像乔恩·斯图尔特(JonStewart)、演员杰里米·皮文(JeremyPiven)以及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明星接球手麦克·皮耶萨(MikePiazza)这样的有钱人。一家设计师品牌的床上用品店在湿地保护区那些舞台跳水和碰撞舞者曾经嚣张过的一楼位置已经经营了好几年。
邦德街咖啡馆如今成了邦德街酒店,一家时髦的寿司店。在这里可以买到16美元一杯的精致鸡尾酒,另外在这栋建筑楼上的专属居住单元的平均租金已经超过了每套公寓每月10美元。
左图:凯撒·拉米雷兹和莱尼·贝德纳兹在邦德街咖啡馆的旧址前。右图:肯特·米勒和他哥哥在同一个地方展示他们乐队的密纹唱片。90年代他们都曾在这个地方演出,后来这里被豪华公寓和高端寿司店置换了。
一家约翰·瓦维托斯精品店(JohnVarvatosboutique)现在坐落在CBGB曾经繁盛了30年的旧址上。这家高端零售店的老板适当地保留了俱乐部原本识别度很强的通风管道——这些管道像补丁一般贴满了许多年来的各种乐队的宣传贴纸。墙上也用画框装裱了难以计数的部分破损的拼贴画,而这些画都是由各种演出的宣传单组成的。逛店的人可以在配备了收银机的原CBGB吧台花80美元买到一件印有枪花(GunsN’Roses)图案的T恤衫。
流浪者(Tramps)、罗克西、针织厂(KnittingFactory)、布朗尼(Brownies)和玫瑰园舞厅(RoselandBallroom)以及其他几家曾经预约过纽约硬核演出的空间也都消失了。在年玫瑰园舞厅倒闭的影响下,《纽约晨报》宣告这个城市“曾经充满故事的现场音乐气氛”已经完全消亡了。“公寓取代了俱乐部,”这篇报导继续写道,“舞池里那些挣扎着的艺术家已经被欧洲银行家们取代了。”而下东区那些曾经欢迎硬核乐队演出的场所聚集的家园,如今成了年之后城市士绅化(gentrifying,也作缙绅化,指原本是普通甚至贫困居民居住的空间被中产阶级化的过程)最快的区域。
近期在曼哈顿鲍威利区约翰·瓦维托斯精品店拍摄的照片。这家零售店坐落在CBGB的旧址上。上图: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乐队的肯特·米勒正在浏览店内展示的纽约硬核与朋克摇滚的演出宣传单。中图:位于鲍威利区的约翰·瓦维托斯精品店内部。下图:莱尼·贝德纳兹,凯撒·拉米雷兹与肯特·米勒(从左到右)正在这家店里追忆当初在CBGB的演出。
“一旦纽约硬核失去了它的家园,你就无法在每周末再看到同样的人群了,”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的迪恩·米勒如是说。“之后你就和人们失去了联系,那些曾经坚实的土壤也变得很脆弱。”
举例来说,凯文·吉尔在14年前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皇后区白石镇去了旧金山。他这一举动也结束了对SFT(为团结而努力)唱片厂牌本就有限的资助。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从事电子游戏产业,也曾经参于过独立摔角联盟的活动,他的角色主要是评论员,后来他又办了一个专门致力于他这些兴趣的网络电台,当然也聊硬核。
吉尔也仍然在销售一些来自他做SFT厂牌时留下的硬核商品。去年在VOD(失序的视野)20周年纪念日时,他重新发布了VOD的单曲碟《依旧》(Still)”。“我不是在谋生,而是在凑房租,”他说。
还有另外一股针对硬核的力量,一旦人们发现这个音乐门类还有利可图,就会有大量模仿者一涌而入。许多这样的乐队写了一些更简单却更充满攻击性的硬核音乐,在90年代末期这种现象变得非常普遍。凯文·卡斯特,前任高堡演出的预约员说,“有一种硬汉姿态的意识形态进入了这种音乐。我确定大部分去看演出的人并不想伤害别人,但是绝对有一小部分例外。”
莱尼·贝德纳兹,华氏度的前成员也认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看到越来越多打着碰撞舞者旗号的“贱货”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伤害别人”,这样硬核乐迷去看演出就不得不再三犹豫了。
莱尼·贝德纳兹,华氏度的前任吉他手,指着约翰·瓦维托斯店里展示的一张经典招贴上他们乐队的名字。这家店位于曼哈顿鲍威利区CBGB旧址上,贝德纳兹曾在此演出过。
与80年代纽约硬核形成期类似,许多人都是在他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卷入那些过分活跃的90年代硬核运动的。等到日历翻到年的时候,许多乐队成员与乐迷之类的人都像是接到了叫醒电话一样突然清醒了。
“在那个年代,伤痕是荣誉的勋章,”卡斯特在谈到90年代的时候说,“但是当你成了一名机械师或其他需要用双手来做的工作时,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你就不能因为在演出现场受伤而两个月不工作了。”
卡斯特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解释为什么纽约圈子会失去光泽。“我觉得真正的衰退是从9/11开始的,”他说,“整个城市充斥着一种压抑的情绪。人们不敢出门。”他补充道,尽管许多演出都是为了帮助受害者家庭集资而举办的,出发点都很好,但是这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的现况。在恐袭之后几个月里,卡斯特与城里各个俱乐部的老板都聊过,这些俱乐部的境遇都和原来的“高城”差不多——“高城”在年11月关闭了,因为房东不愿意让俱乐部再超负载运营。
尽管受够了的克雷格·塞塔瑞自认为是这个圈子的主要支持者和发言人,但当谈到这种音乐风格和社团的长期财政能力时,他还是坦言道:“不论我们如何讨论暴力,这种文化潮流(硬核)也都难辞其咎;这绝不是一种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交流媒介;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种伟大的美国亚文化。”
弗兰克·帕维奇没有因为他在年所拍摄的那些乐队和俱乐部的消散而哀恸,他现在是一个瑞士日内瓦居民,他正忙于制作他的第三部全长纪录片——希望借此来庆祝这种音乐风格的恢复力以及由这种音乐所引发的人与人的联结。“这简直就是在今天依然没有被大众媒体所腐蚀的唯一的东西,”他说。“这种文化不会妥协,今天当你看到走在大街上的某人穿着纽约硬核的T恤衫,感觉依旧是屌炸了。”
年,硬核音乐圈的一些人摆拍的照片。上排,从左至右:受够了的贝斯手,克雷格·塞塔瑞;疯球的主唱弗莱迪·克莱西恩;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解毒剂的主唱,德鲁·斯通;愤怒五人组的斯提克曼(Stickman)。下排,从左至右:生化危机的主唱和贝斯手,埃文·宋飞(EvanSeinfeld);疯球的贝斯手奥雅·罗克(HoyaRoc)。(照片由德鲁·斯通提供)
在今年春天的“黑蓝碗”大会上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T恤,许多花白山羊胡子的光头穿着这样的衣服,遮盖着20年前并不存在的大肚子。这个盛会的前身是“硬核的超级碗”,这是个一年一度在东村的利兹旧址上新建的韦伯斯特大厅(WebsterHall)举办的全天候盛会。在这里,没有那些带着链条钱包和满身口袋的板仔裤的小孩,我怀着浓浓乡愁游荡在这光线黯淡的演出空间,邂逅着那些15年前我曾在高堡给调过音的乐手,并与我的那些音乐大英雄们握手打招呼。
疯球的发言人,现年40岁的弗莱迪·克莱西恩第一次登台是在他7岁的时候,他的继兄,不可知论前沿的罗杰·米雷特(RogerMiret)让他上台来为乐迷唱歌。他是“黑蓝碗”的主办人之一。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的肯特·米勒参加了今年的“碗”会,他说这个聚会还在“维持着硬核圈的活力”。
短暂的开场之后,韦伯斯特大厅就开始跟随着退路(Leeway)和疯球开始摇滚了,这两个乐队都成立于80年代,从此火爆在舞台上。一个巨大的碰撞舞圈在大厅里张开了,尽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还是不小心注意到有几个哥们已经撑不住了,上气不接下气(必须承认的是,如果我在加入到他们中间,我一定不会这样)。
克莱西恩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一个四岁,另一个四个月。他回忆起年轻的时候与疯球一起去演出,他从不在乎音乐的商业经营。但是“做一个硬核仔并不能付账单”,他现在知道了,在这个圈子里混了33年的克莱西恩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风格的纽约硬核“代表人”与“策展人”。
“人们总是很在意乡愁的因素,”他谈到硬核现在的境遇时总是很感伤,现在要不就是有人想要对这种文化进行资本化操作,否则几乎没人对这种音乐风格感兴趣了。“我不想变成一个怨妇,”他继续道,“我支持任何支持我的人,但是现在的人都随大流了。”
在下东区的邦德街咖啡馆旧址前,维吉尼亚·克雷斯举着一张她收藏的经典七英寸纽约硬核密纹唱片。
维吉尼亚·克雷斯和她当年收藏的疯球的唱片
维吉尼亚·克雷斯时不时依然会去看一些演出,近期她看了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与疯球的同场演出。她说一些朋友在回忆那夜时,评价那天的演出“就像又回到了年一样”。
“那就是纽约最后的疯狂时光,”克莱西恩说,之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就要“带着一堆狗屎离开了”。但是有一些征兆预示着另一次重生的可能。
三年前,本·拉特利夫(BenRatliff)在《纽约时报》里写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纽约看到硬核现场展示出这么强大的能量了。”《生效杂志》(InEffect)是一本顶级的硬核爱好者杂志,杂志的出版人克里斯·韦恩(ChrisWynne)曾经自己亲手将印好的杂志送到唱片店去,后来他又将这个杂志转移到了线上。他说过,“纽约有成吨成吨的乐队”。此处他指的是分离之种(ABreedApart)、操控(Manipulate)、痛(Ache)、常规化(Regulate)、活得比死神久(Out.Live.Death)以及Enziguri(一个模仿摔角招数日文发音而由主唱Davey发明的词,后来他得知这个词完全没有任何意思)等一些更值得注意的刚发了新小样的乐队,尽管他们还没有获得唱片签约,但还是吸引了一些更年轻的粉丝加入到这个社群里来,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了今年的“蓝黑碗”。
对于迪恩·米勒和无法挽回的社会价值而言,当事关这个他已经参与了30多年的社群之时,时间和地点并不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都没有了,所有乐队,所有演出空间都没有了,硬核也被全世界禁止了,我的乐队伙伴仍然会聚集在我家地下室玩音乐,”他说。“我们从没有加入什么飞镖协会或者保龄球联盟。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硬核。”
有关作者:
麦克·斯塔尔,纽约皇后区的自由作家、编辑以及记者,他的作品已经出版在许多印刷与数字出版物中。
“利维坦”(刘云涛白癜风外用的有什么特效药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wh/5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