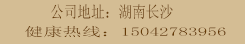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美食 > 周边动态ldquo陆地换海洋r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美食 > 周边动态ldquo陆地换海洋r

![]()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美食 > 周边动态ldquo陆地换海洋r
当前位置: 文莱 > 文莱美食 > 周边动态ldquo陆地换海洋r
二战后独立的文莱和马来西亚之间曾长期存在领土争端。该争端源于英国殖民者对北婆罗洲地区的英属殖民地实施的较为模糊及不合理的划分,情况较为复杂。为了实现和平稳定的边界,独立后的两国通过马拉松式的长期谈判,令这一争端以和平的方式悄然得到了解决。
文马两国的争议领土由海陆两部分构成,陆上部分为林梦地区(LimbangDi-vision)的主权归属争议(面积约平方千米),海上部分为两国在南海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议。两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谈判,解决了彼此间的海上划界纠纷,并于年起着手进行联合陆地勘界。这是东南亚地区首个经由当事国通过双边和平谈判形式得到一揽子解决的领土争端。尽管当事国未公布这一争端的具体谈判细节和协议内容,但从公开报道可以看到,文莱放弃了对林梦地区的主权声索,与此相应的是,马来西亚在海上争端方面作出了让步,同时,两国设立了海上联合油气开采区。
既有研究中,仅国外存在少量对文莱与马来西亚领土争端的专门研究。哈勒特罗斯特(Haller-Trost)的研究较早,他从地理、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缜密分析了两国陆海领土争端的起源、声索现状,并据此推断了可能的解决结果。克里斯威尔(Crisswell)从历史的角度对林梦地区争端的由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魏德碧(Weatherbee)、辛格(Singh)和弗朗西斯(Francis)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简单介绍了林梦地区争端及与争端有关的文马两国的历史。国内尚未有针对此争端的专门研究,目前只有邵建平的硕士论文简要提及文莱与马来西亚领土争端中林梦地区争端的缘起和解决结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两国的公开信息,分析文莱与马来西亚领土争端所受到的国际法约束,并进一步探析影响两国达成最终解决方案的深层次原因。
一文莱与马来西亚领土争端的历史渊源
文莱和马来西亚争夺的陆上领土———林梦地区位于婆罗洲岛(亦称加里曼丹岛)北部海滨,现属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版图呈狭长马蹄形,将文莱陆地领土分割成互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中间间隔西文莱湾,其中西文莱湾海域大部分属文莱领海,西南角一小部分为林梦地区领海。该地区包括三县一镇,分别是:林梦县(LimbangDistrict)及该县北部海滨的兰高镇(RangauTown)、大老山县(Terusan/TrusanDistrict)和老越县(LawasDistrict)。两国的海上领土争端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争议,部分南海岛礁争议,以及与林梦地区主权归属相关的西文莱湾领海争议。两国的海上划界最早源于年英国颁布的北婆罗洲和砂拉越殖民地的边界法案;双方都基于《年法案》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文简称《公约》)主张各自的海上领土。
19世纪林梦地区被英国殖民者蚕食是文莱和马来西亚领土争端的源头,并且该地区的主权归属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两国的海上领土争端。这一时期林梦地区各县的主权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砂拉越和英属北婆罗洲公司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通过强迫手段逐渐割占。英国殖民者詹姆斯·布鲁克(JamesBrooke)于年从文莱割占砂拉越,随后成为砂拉越国王。年,因反抗文莱中央政府的过渡税收政策,林梦县地方酋长发起叛乱。英属北婆罗洲公司在同时期除向文莱取得林梦地区以东的北婆罗洲领土外,还强行获得干预文莱变更林梦地区领土主权的权力,对文莱形成威胁。年11月被文莱苏丹任命为林梦县摄政的哈辛(Hashim)由于无力镇压叛乱,且试图使砂拉越与英属北婆罗洲公司相互制衡,从而保证自己在文莱王国的其他利益,有意将林梦县和大老山县割让给布鲁克,并交由后者镇压。
此后,由于林梦县地方权贵的支持和英国的背书,文莱通过协议正式有偿将林梦县及该县北部兰高镇割让给砂拉越。除林梦县与兰高镇外,大老山县和老越县在同一时期由哈辛被迫割让给英国殖民势力。年12月,哈辛将大老山县有偿割让给布鲁克,同时英国对此作出背书。年9月,苏丹哈辛将大老山以东的老越县有偿割让给英属北婆罗洲公司;3年后,英属北婆罗洲公司将老越县有偿转让给砂拉越。由于英国于年将砂拉越和文莱变成保护国,老越县的主权变更是由英国安排在两国的摄政所主导,因此英国在实际行动上为该县的主权变更作出背书。加入,文莱政府就不得不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共享石油开发的利润,并且,尽管文莱苏丹本人有机会成为名义上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之一,但联邦内部还同时存在其他来自马来半岛的苏丹,文莱苏丹的权力会因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选举制而被相对削弱,文莱最终谢绝了这一邀请。年马来西亚从英国独立,包含林梦地区在内的砂拉越殖民地自然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文莱当局在文莱独立前长期对此保持了沉默。与此相反的是,从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文马两国三次就海上领土发生过纠纷,包括:马来西亚扩大大陆架范围的举动遭到文莱的抗议;马来西亚占领南通礁的举动遭到文莱抗议;两国在争议采油区短暂对峙,该区域位于文莱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也在中国主张的“九段线”范围内。
年和年,文莱依据《年法案》先后公布三份地图,提出其大部分海陆领土范围的主张,标志着两国领土争端明朗化。文莱在独立后提出这三份地图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和明确其领土范围,并针对争议领土向邻国公开其主权主张,继而与邻国确定清楚的边界,保障自身边界稳定和安全。第一份地图为文莱主张的领海和近海部分大陆架范围,其中林梦县外海附近水域被标注为非文莱领海。后两份地图都提及林梦地区争议。第二份地图为文莱主张的大陆架范围,其中注释明确提到:“此图所示海洋界线尚未与邻邦通过划界协议达成一致。西文莱湾海域界线(的划定)须依据林梦县及相邻的老越县、大老山县和兰高此后,直到年从英国独立,文莱实际统治的领土范围基本固定下来,这期间林梦地区处于砂拉越行政管辖范围内,砂拉越主权归属的变化事实上包含了林梦地区。文莱政府没有公开抗议英国和马来西亚实际统治林梦地区的任何行为,而仅抗议过马来西亚对两国有争议的部分海上领土的主张。年7月,布鲁克治下的砂拉越被并入英国,成为英属殖民地。8年后,英国颁布《年法案》,规定英属婆罗洲地区各殖民地边界。20世纪60年代初,马来西亚联邦在筹备独立过程中曾邀请文莱加入,时任文莱苏丹奥玛·赛义夫丁三世考虑到一旦镇等争议领土的最终结果。”第三份地图为文莱主张的渔业区范围,其中的注释再次提到林梦地区争议,并说明文莱主张的渔业界线无损于它对“林梦县及相邻的老越县、大老山县和兰高镇的声索,以及其他任何相应的海上声索。”
针对领土问题,文马两国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双边谈判。目前,关于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详细的官方资料还难以找到,两国鲜有公开具体谈判内容,并且双方对于国内、国际舆论都采取低调处理和模糊应对的态度。但是,从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双方谈判的大概进展:年,两国就争端开启了零星的会谈;年,两国开始举行针对领土问题的双边会晤;年2月,两国同意就海上共同勘界成立联合委员会;年3月,两国就最终解决领土争端签署和互换外交照会。随后马来西亚总理公开表示文莱放弃了对林梦地区的声索。两国不仅确定了海上界线,还原则上确定了林梦地区划界和勘界的“模式”(modali-ties)。此后,两国于年3月达成联合勘界协定,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巩固双方的领土划分共识,成立“联合陆地边界技术委员会”,并开始进行边界共同勘测。
二文莱和马来西亚领土主张的国际法约束
国际法中有三个衡量争议领土归属的原则能影响争端当事国对林梦地区主权法理状态的判断,包括占领地保有原则(PrincipleofUtiPossidetisJuris)、有效控制原则(PrincipleofEffectivité)和默认原则(PrincipleofAcquiescence)。两国的海上划界主张则受《年法案》和《公约》的约束。国际法的法理不支持文莱的陆地领土主张,而支持它的海上领土主张,马来西亚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首先,尽管西方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塑造了殖民地的边界,但这些殖民地从原殖民母国独立后往往直接继承此前的边界。这个不成文的惯例———占领地保有原则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莱对林梦地区主权的声索。这一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美洲各独立国家直接继承西班牙殖民者所划定的边界。国际法院在数个判例中都承认了此原则对判定新独立国家边界的有效性。尤其在几内亚比绍和塞内加尔海上划界案中,国际法院甚至通过直接引用东南亚地区国家间的海上划界方式对此原则加以阐释和肯定:“二战后亚洲新独立国家,例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的地图显示海上界线源于殖民地时代。”
文莱在年前基于长期有效的管辖而拥有对林梦地区的原始权利,尽管这种管辖受当时技术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仅仅表现为向地方权贵和普通居民征税,任命地方官员,以及通过暴力机构管束各县居民等较为原始的、类似于羁縻统治的形式。虽然布鲁克治下的砂拉越和英属北婆罗洲公司割占林梦地区各县的行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胁迫,孱弱的文莱政府几乎无力反对外国殖民者,但文莱苏丹及贵族接受了前者的补偿。考虑到时际法原则,不论此补偿是否合理,这种割占行为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即使文莱官方试图以条约不平等为由否认英国殖民者占有林梦地区的合法性,但也很难找到法理支持。从文莱年颁布的官方地图可以看到,尽管文莱认为林梦地区主权存在争议,但该地图的部分细节体现出它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直接继承殖民地边界的惯例所带来的边界现状,例如没有将林梦县在西文莱湾的内水标注为文莱所有,以及基于实际控制领土的现状,而不是基于它拥有林梦地区主权这一主张划定它的海上界线。
其次,有效控制原则和默认原则使得林梦地区被划归砂拉越后,即使在占领地保有原则无效的情况下,文莱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也难以得到国际法的支持。根据有效控制原则,一国对争议领土须有意愿并实施有效展示主权的行为,包括行政管理、立法等形式,以体现其实际控制该领土,并且此行为必须是和平的。和平地控制争议领土意味着当事国对该领土的任何行使主权的行为至少没有受到争端对手国的公开抗议或反对。如果对手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公开质疑,则“默认”了该当事国对争议领土的有效控制。从年到年,整个林梦地区都处于砂拉越(包括布鲁克治下的砂拉越、英属砂拉越殖民地和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实际控制下,而文莱官方并没有公开抗议。这种实际控制不仅表现为对林梦地区人口的管理,随着后来技术的进步,该行为也逐步多样化,包括马来西亚对相关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对该地区行政建制实施的大规模的变更等等。
虽然文莱国内对林梦地区主权的争议表达过质疑,并且林梦县境内也出现过希望复归文莱的民间运动,然而文莱官方在长达80余年时间里并没有公开反对或抗议过林梦地区处于砂拉越治下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即使英国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林梦地区的行为非法,同时英国作为保护国对此所做的任何背书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文莱长期的默认也使得林梦地区的主权以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被转移至砂拉越。不仅如此,文莱在年正式提出与马来西亚存在领土争端时,它的官方地图仍然采取遵守实际控制现状的画法。如果文莱主张林梦地区的主权,则它应在地图的海上界线主张中明确体现出来,例如把林梦县在西文莱湾的领水划为己有,以及基于林梦地区东部老越县的辖地将它主张的东部海上分界线东移。基于马来西亚长期的实际控制和文莱长期的默认,国际法原则更支持马来西亚方面对林梦地区的主权主张。
最后,两国的海上领土主张基于《年法案》中的海上界线和《公约》中关于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规定,它们的海上领土争端受到这些条约的约束。这些法案和国际条约主要支持文莱而非马来西亚的海上领土主张。英国提出《年法案》是基于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其中根据《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十二条中的中间线原则划定了砂拉越和文莱所属海域之间的分界线,根据《大陆架公约》第一条规定了各殖民地大陆架范围。此后,马来西亚只是于年单方面延展其大陆架范围才遭到文莱的抗议,但马来西亚的海上主张此时尚未越过两国的海上分界线。
马来西亚第一次越过两国海上分界线主张海上领土的行为是单方面占领南通礁,第二次是抗议文莱单方面批准外国公司在争议油气区采油并展开短暂的海上对峙。尽管《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和《公约》都规定相邻两国的海上分界线可以根据历史性权利和其他特殊情形而不须严格依照中间线原则划定,但英国早在文马两国独立前就已基本划定此界线;马来西亚主权继承自前英属殖民地,它的海上权利主张原则上亦不能越过此线。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文马两国依据《公约》声索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必然会与中国、越南等南海声索国的主张重叠。马来西亚于年提出专属经济区主张,但并未出具相应的地图,一定程度上是考虑到南海争端的复杂性而有所回避。与此相似,文莱也没有提供它主张的完整的大陆架信息,这给予马来西亚越线声索的机会。尽管如此,在不考虑南海争端其他声索国的主张,而只考虑文马两国主张的前提下,根据《公约》的规定,两国的海上中间线必然可以延伸至海里处,因此马来西亚的越线声索无法得到《公约》的有效支持。
三文莱和马来西亚达成妥协的深层次原因
国际法部分原则和部分国际条约约束了两国各自对争议领土的主张,但这仅仅是两国达成原则性妥协的法理基础。文马两国仅通过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还不能明确两国争议区域的具体范围和项目,为了达成最终的妥协,还需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就一些细节,如某一部分争议领土的归属、精确的海陆界线坐标,以及具体的油气开采区域等进行缜密的谈判和论证。在繁琐的争端谈判过程中亦有可能出现因当事国不愿严格按照国际法进行谈判,或就争议领土某一项目发生争执,或某一当事国国内反对意见强大到对中央政府的谈判形成掣肘,而导致争端解决进程被阻断的情形;这些风险可能导致两国谈判失败,从而使争端被搁置而无法得到最终解决。从结果可以看到,两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谈判才达成最终的分割方案。它们之所以能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通过双边协商的形式实现最终的妥协,离不开更深层次的人文、经济以及政治原因,具体而言,包括:两国紧密的人文、经济关系使得双方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双方就不同争议领土的利益需求使得它们能够达成争议领土的分割方案;双方通过妥协和海上资源共同开发形成一致的南海主张,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
首先,文莱和东马来西亚有非常紧密的人文和经济联系,这是文马两国和平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也使得两国更倾向于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领土问题。历史上,东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和沙巴两州大部分地区曾属古文莱王国的一部分,与现代的文莱国有相同的人文历史,它们与西马来西亚差异相对更大。尽管英国殖民者后来在这两地分别建立了殖民统治,但两地与文莱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民间联系,这些联系包括贸易、航海、劳务、旅游等民间往来;其中林梦地区是东马来西亚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大量人口长期在文莱从事劳务工作,主要经济产业为农业、林业和旅游业,林梦地区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依附于文莱。由于北婆罗洲岛人口主要分布在宜居的沿海平原地带,岛屿中央为人口稀少的山地,加上文莱和林梦地区交错的行政版图格局,从殖民时代至今,文莱成为整个婆罗洲岛北部地区交通网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扼守砂拉越和沙巴两州陆地与海上交通的要道。
作为小国,文莱自独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其核心目标是维持主权独立和促进经济发展。该国尤其重视与东盟成员国间的紧密关系。文马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国力差距。马来西亚在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远强于文莱,并且是文莱唯一的陆地邻国。对于文莱而言,维持与这一实力远强于自己的邻国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保障本国的安全。如果两国因为领土争端发生冲突,文莱会面临一个充满敌意的马来西亚,且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后者潜在的海上与陆地双重威胁,然而文莱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和资源禀赋应对这样的风险。作为小国,文莱优先通过和平的方式处理与这一邻国的争端是明智之举。
与文莱相似,虽然马来西亚的国力在东南亚地区位居前列,但其对外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总体上也较为温和。从马来西亚处理与新加坡和印尼的领土争端可以发现,该国倾向于通过双边和平的方式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议,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会根据具体的事态选择特定的策略,其政策灵活度较高,偏向实用主义;如果通过对峙和冲突不能达成既定目标,马来西亚会转而采取其他策略。对于马来西亚来说,考虑到文莱是扼守砂拉越和沙巴两州之间的交通要道,并且东马来西亚靠近文莱的地区,特别是林梦地区与文莱在经济上有较大的依存关系,马来西亚与文莱交好能保证东马来西亚地区交通网络的安全,进而保证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由于两国的对外政策都较为和平,因此它们更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其次,争议领土所包含的利益是文马两国争夺的重点,两国分别在陆地和海洋领土中所期望的利益不同,这使得双方能够就争议领土分割达成妥协。两国的争议领土中,林梦地区的经济价值相比于南海油气资源来说较小。与北婆罗洲其他地区类似,林梦地区经济相对较好、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是沿海平原;然而这些沿海平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不高,传统农业是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与林梦地区相反的是,文莱外海区域属于南海南部的文莱—沙巴沉积盆地,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文莱在近海大陆架的油气开采活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石油开采高峰时期曾达到平均每天24万桶;海上油气开采和销售成为文莱的经济支柱,也使得文莱成为东南亚第三大产油国和世界第九大液化天然气输出国。依靠石油经济,文莱已成为世界人均国民产值最高的国家之一。
作为人口较少和未经历充分现代化发展的小国,文莱没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本进行国土资源开发。该国的海上油气资源开采尚完全依赖英国和荷兰的公司,即文莱官方授权这些外国石油公司进行近海油气资源开发,文莱政府作为资源提供方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这样的收益足以使得文莱一跃成为东南亚仅有的两个富国之一。假设林梦地区主权被文莱收回,文莱几乎无技术实力对该地区实施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而文莱开采南海油气资源的时间较长,并且已经较为成熟,因此相较于油气开采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开发林梦地区的投资回报更显得微不足道;不仅如此,文莱还需要对该地区收入较低的农业人口进行经济扶持。
在国际法原则基本不支持文莱对林梦地区主权主张的情况下,文莱向马来西亚声索该地区主权的动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谋取利益交换的手段。由于林梦地区主权归属存在争议,马来西亚如果要维持争议领土实际控制现状就必须与文莱进行妥协,而作为交换,它就需要在其他领土争端,如海上领土争端方面做出让步,因为国际法不支持它的部分海上主张。对马来西亚来说,维持对林梦地区的管辖意味着东马来西亚两州在陆地上相互连接,避免了两州在地理上被分割的情形,从而保证东马来西亚地理上的连续和完整,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两州之间陆上交通的安全。从两国实际达成的领土分割方案可以明显看到,两国基本按照“陆地换海洋”的方式实现了妥协,并且文莱还进一步在海上油气开采方面对马来西亚做出让步,即划定两国联合开采区域。这一方案满足了双方各自的主要利益,同时也实现了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此外,最终解决方案的达成使得两国的关系更进一步,并使得领土问题不再成为两国潜在冲突的诱因,保障了本地区的安全。
最后,文莱和马来西亚的领土分割方案包含海上联合油气开采区,这一方案一方面可以解读为作为小国的文莱在利益上对马来西亚作出更多的让步,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两国共同应对中国南海主张的策略。由于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在靠近北婆罗洲地区的两段临近该地区海岸线,两国的联合海上油气开采区作为文莱主张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位于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水域内。换句话说,
这一区域理应属于中文和中马争议区域,不能由两国擅自划定,按照国际法,中国的意见必须得到充分的考虑;但文马两国并未如此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一定会遭到中国的反对。
文马两国在争议海域进行联合开采的意图不仅是谋取油气资源利益,也是在应对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形成合力,共同以这种低调、温和的方式对抗中国的南海主张,并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文莱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南海利益诉求与马来西亚的诉求进行了绑定,保证马来西亚支持它的南海主张;与此相应的是,马来西亚也借此换取文莱对它的南海主张的支持。两国在南海不仅越过中国的“九段线”声索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还各自声索并实际控制一定数量的南沙岛礁。中国主张南海问题需通过一对一的双边谈判得到解决,拒绝多边谈判。文马两国达成妥协并形成合力共同应对中国的南海主张,对它们来说,优于各自单独应对中国压力的情形。这一做法对它们有利,也是它们试图给中国解决南海“九段线”内东南部区域的领土争议设置的障碍,使中国在面对这一区域的争议时不得不同时考虑马来西亚和文莱的诉求。
结论
文莱和马来西亚经过长期的协商最终达成了两国分割争议领土的妥协方案。这是东南亚地区首例经由当事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的领土争端案。在这个争端中,文马两国基本按照“陆地换海洋”的方式进行妥协,即文莱放弃对陆地领土———林梦地区主权的声索,换取马来西亚在海上争端中的让步。国际法中有数个原则约束了两国对林梦地区主权状态的衡量,同时,数个国际条约约束了两国的海上划界声索。尽管如此,国际法仍只能为两国解决领土争端提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文马两国在此基础上实现相互的妥协是基于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两国间紧密的人文和地缘经济关系使得双方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领土争端;两国分别在陆地和海洋争议领土中的不同利益需求使得双方容易就争议领土分割达成妥协;两国通过海上资源的共同开发实现双方南海主张的捆绑,并在南海争端中共同应对中国。文马两国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为该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借鉴方案,也为中国了解本地区国家如何解决彼此的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戴渝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专业级博士研究生,—年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
文章来源:东南亚研究,年12月第6期。
转载请注明:http://www.wenlaia.com/wlms/5071.html